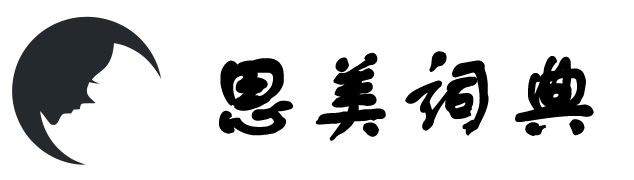等裴宝善闻讯而去,只看见崔鹤亭病倒在榻上,面色惨白,双眼紧闭,不住地发汗,跪了一地的太医,谁都不敢出声。
裴宝善瞳孔紧缩,呼吸都急促了,甚至有些慌乱无措,“崔鹤亭。”
无可否认地,她讨厌皇帝,也恨太子。
可当她看到崔鹤亭,那样在皇权里长大的崔鹤亭,并没有坏心,甚至是纯良的,温善的。她宁愿他坏得彻骨,恶毒到骨子里,是世界上最草菅人命的纨绔。
可崔鹤亭不是,偏偏不是。
“崔鹤亭!”裴宝善跌坐在塌边,握住崔鹤亭冰凉的手指,强忍着泪水,一时不知道如何裁决。

“宝善,”崔鹤亭缓缓睁开眼,稍稍侧了侧头,与她额头相抵,呼吸交错,他阖上眼,好似用尽全力,“裴宝善,我做了个梦给你。”
“我梦见你平平安安地长大,我梦见你哥哥没死,我梦见……我梦见你没嫁给我,”崔鹤亭断断续续地说。
好像用尽了全力,他盯着裴宝善,执拗地道:“父皇教我掠夺,教我狠厉杀伐,教我喜欢的要藏在心底,然后不择手段地抢过来……”
“可是只要一看到你,我竟只想成全。”
“裴宝善,我爱你啊。”
裴宝善心尖一颤,汹涌地爱意烧起她心间的死水,燃成一片旷阔无边的海域。
她忽然握住崔鹤亭的手腕,伏下身咬破他的指尖,吮了一口鲜红的血,不知道在对谁说:“你是我的夫君,你死了,我殉你。”
“小姐!”松子急不可耐地大喝。
裴宝善回过头看她,唇珠上还凝着猩红的血,唇红齿白,却同她的目光一样渗人。
松子不敢将裴宝善赔进去,在她的手脚下,次日太医就配出了方子,崔鹤亭的病大有好转,夫妻二人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只不过裴宝善的母亲没两日就自戕了。
但变故更大的是皇帝忽然驾崩,朝中大臣拥立太子登基,整个朝廷都乱了。
在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喧闹中,裴夫人的死好像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这样一件小事,还是一寸寸压弯了裴宝善的腰。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401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