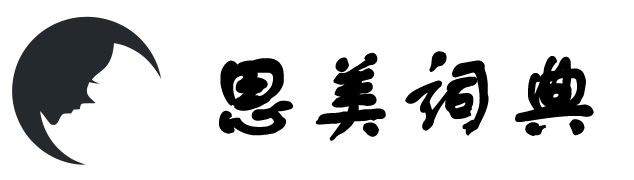崔鹤亭侧目看了她两眼,把她的那碟梅子挪过来,把自己的蜜饯递过去,她好似也没觉得不对,时不时捻两枚入口。
崔鹤亭一开始还耐着性子等她说话,可裴宝善死活不肯开腔,崔鹤亭眼风不停地扫她,问:“一群庸脂俗粉,好看吗?”
“妾身倒是瞧着个个都很不错。”
崔鹤亭又把自己的蜜饯抬回来,把她的梅子端过去不肯搭声。

他酸得紧,却不肯说。
可蜜饯甜丝丝的,很好吃。
回府的时候,裴宝善替他拍落肩头的雪,如同寻常夫妻一般,说:“殿下身为储君,担旁人不能担之责,扛着大宣的将来。如今国将不国,殿下……还当勉力。”
裴宝善看得很清醒,歌舞升平的表象,掩盖的是白骨累累的疮痍,国难当头,皇帝还顾着寻欢取乐,太过愚蠢。
崔鹤亭并不坏,甚至算个贤王,只是被权贵浸软了骨头,有些养废了。可他到底年轻,十几岁的年纪,也强求不来什么。
可这样怨声载道,动荡不安的年岁,他的身份便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
三
裴宝善这样舒坦的日子还没有持续多久,她的父亲就死了。
她吃斋念佛,戒掉荤腥,闲暇时日也在翻译佛经,像个带发修行的姑子。
可她这样虔诚的信徒也没有感动到佛祖,她的父亲最后还是死在了两军交战的时候。
那是裴宝善第一次失态,她劈手就给了崔鹤亭一掌,指着他破口大骂,“如果不是你!我父亲不用上战场,我也不用嫁给你!崔鹤亭,你和你的父皇一样,都是扶不起的阿斗!”
“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为你们枉死!”
父亲知道君王庸碌,大宣的国运也算到头了,所以才宁可将她送去出家也不愿让她被牵连,没想到皇帝为了让父亲出征,还是算计到了她的头上。
崔鹤亭的嘴角洇了红,鲜红的血凝在白皙的脸上,鲜明又颓唐。裴宝善横了他最后一眼,好似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你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废物!”
她跨过裙摆,让人收拾行头,回了将军府。
母亲好似一瞬间老了十多岁,她伏在父亲的棺椁上不住地哭。
裴宝善微微一怔,有些恍惚,很多年前,她也这样伏在哥哥的棺椁上哭。
裴宝善不敢过去,只有泪水划过她冰凉的脸颊,她想劝母亲不要再哭了。可她苍白的言语,连自己也劝不住。
她噎了噎,忍痛阖上了眼。裙摆扫过门槛,她不忍再看,只把目光放在屋外,好像心痛地要昏厥过去。
裴宝善是有一个哥哥的,长她三岁,但永远死在了十八岁的隆冬。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40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