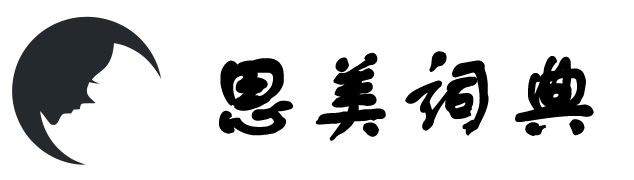他半晌没说话,直到二姐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时,他才拂袖而去,扔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休想躲着我。”
我瞟了一眼他那被拉得长长的影子,总算消失在了门口,整个人吁出一口气。
二姐进来行礼问安,一看见我的红眼圈,当即调侃道:“没想到太后竟是个痴情种,都三年了,一到这个日子,还为先帝哀悼呢?”

我起先一愣,没反应过来这有什么联系?细思之下,陡然醒悟过来——明日是先帝的忌辰!二姐这个宫外百姓都知道,我竟然忘了?!
想起这茬,我的心又被拎起来:每年先帝忌辰,我作为太后,都要同皇帝去太庙上香行礼。
我阖上眼,心虚得要死,万一先帝把我刚刚跟他儿子干了些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在太庙里显了灵……一想到这个,我顿时脸都煞白了,手也止不住的抖。
二姐惊道:“太后,您没事吧?先帝找您来了?”
我忘了,我二姐,京城赫赫有名的沈家姑奶奶,成了三次亲也和离了三次的奇女子,从来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她不吱声还好,她一说这话,我脚底心发凉:“哀、哀家抄点地藏经去,你陪着磨墨。”
先帝忌辰这天,晴朗了好几日的天气突然乌云密布,闷雷阵阵。
俗话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可我怕,我怕头顶上那道雷会稳准狠地朝我劈下来。
我三步并两步,差点崴了脚,揣着昨晚抄得手发麻的地藏经一头钻进马车,没想到里面已经坐了人了。
我抬头瞪着坐得四平八稳的皇帝,又慌又气,今日是先帝的忌辰,他这个当儿子的分明做了亏心事,不仅面不红气不喘,还想搞什么名堂?
“你坐这儿干什么?!”
他也毫不客气地回瞪我:“沈归麓,这是我的车!”
我怔住,难道是因为刚才我怕雷劈,一时慌张钻错了车?我正想退下去,胳膊却被他一把捞住,接着一股蛮横的力道将我拉了进去,还没来得及容我有所反应,他便开口让启程了。
“你还矢口否认,这分明又是存心撩拨我。”
他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喃喃自语:“你就是喜欢我。”
我正手忙脚乱地坐好,听见他这么讲,气得胸口起伏,脸却不争气,腾地红了起来。
碍于外面宫婢太监们的脚步声很是清晰,我只能假装没听见,故作正经地目不斜视,实则拿余光打量这车厢四周。
怎么办,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他若是想对我做什么,我稍一大声,外面的人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办?
马车走了半晌,我只听见底下车轱辘滚动的声音,眼观鼻鼻观心,一声不吭。
太庙怎么还不到,怎么走得这么慢……
我焦心地算着时辰,虽然没有抬头,但能感觉到皇帝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转悠。
说实话,我自小虽在闺中长大,没见识过什么风月情景,但能敏锐地意识到,此时此刻皇帝看我的眼神,绝对不正常。
昨天那场被眼泪救场的对峙,此时又被延续了,偏生我一时半会又哭不出来。
我捏了捏袖子里的手,鼓足勇气,抬头挺胸地看向他,拿出长者的姿态:“皇帝,叫御膳房给你壮阳一事,是哀家不对,往后哀家什么都不插手了,你大可消气。”
言下之意,让他别再搞出些有的没的吓唬我了,我一介未经人事的小寡妇,不经吓,认输总行了吧?
皇家血脉,要断就断吧,我不管了。
第6章
他像是轻笑了一声,并没有答应。
“窗户纸一旦捅破,你再装就没意思了。”
长者姿态端持失败,我的腰杆子突然不硬了,一瞬间,我气得几乎要磨牙,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他台阶他不下,是要跟我杠到底了?
“皇帝,你再执迷不悟,别逼我待会儿在先帝面前训斥你!”
我压着嗓子放狠话,却带着底气不足的颤声儿。
他即位三年,身上早已洗脱了当年仅存的一丝稚气,变得戾气更甚,威严十足,我猜到,他可能也不会把这点威胁放在眼里。
我果然没猜错,他不仅置之一笑,还大放厥词:
“不劳你费唇舌,待会儿到了父皇牌位前,我先认罪。”
我一噎,想看看他脸皮有多厚:“什么罪?”
“轻薄太后一重罪,觊觎太后一重罪。”
我的手指尖捏着袖口,捏得指节发白,这个狂妄的小子,明明脑子清醒得很,也知道这是大逆不道,如今一脸“我还敢”的不屈,没有一丝忏悔,算什么意思?
他见我杏眼圆瞪半个字憋不出来,又斜斜弯了唇角:
“如果你觉得梦中亵渎你也算罪,那我再多认一重。”
等我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时,脸已烧得发烫。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379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