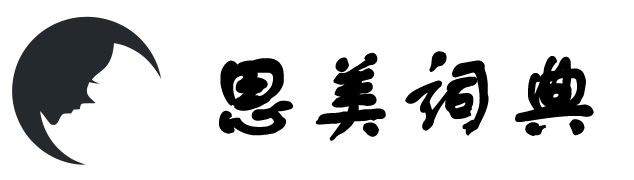纵是多年后的海清河晏,亦扫不清战争的伤痛和肃杀,抚不平世间亡灵的哀怨。
我悲悯世人,却也身陷泥淖不得挣脱,终无力渡他人于苦海,何况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将一切不该起的心思抛之脑,夜路漫漫,仅靠着手中的夜明珠照明,四处只有马蹄飞驰而过所留下的土坑,却没有打斗的痕迹。
「长公主权倾朝野,又何致于率兵至此不毛之地,自讨苦吃?」

「当以自苦为极。」我一愣,随口答道。
「我倒不知公主竟有如此慷慨心境。」张御息从暗处走出来,声音带着莫大的讽刺,「托岑将军的福,您还是来赴约了。」
「他人呢?」我按着腰间嗡嗡作响的长剑,眯起眼睛打量他。
他一身白衣,头顶上好的白玉头冠在夜明珠的暗光下变得透透的,衬得那一双原本淡漠的眉眼更加无情。
我曾见过他一面,在烟山居士那。
他与秦慕向来交好,时常上山寻他议事,这一来二去的,我也便算是跟他面熟了。我原以为秦慕已经算是冰山了,却没料到他比秦慕更加深不可测。
北黎少年丞相,自小便是被别人称为神童长大的,能走到这一步的,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我自然没有想着他能告诉我岑晟在哪,手心冷汗将剑柄浸湿,夜风又将手心吹得凉凉。
我就和他对峙着。
「岑将军降了,还有他的一列人马。」他轻轻一笑,淡淡扫了眼我手中的剑,「公主若问他在哪,自然是在西狄。」
「荒唐!」我轻嗤一声,「张御息,本宫敬你是北黎的前相,卖你几分面子,还真蹬鼻子上脸了?」
「虽说你向了秦慕的打扮,一身白衣衣冠禽兽,七窍玲珑不分彼此,可若是西狄那方知晓你们这出狸猫换太子,你觉得你们是否会得到想要的五座城池?」
我厉声威胁他。
他只是轻轻把玩着手中的折扇,浅色的眸子斜睨着我。
我将注意力放在了他手中的折扇中,那是上古机关术所造,外观看着平平无奇,可其间九九八十一跟银针,每一根都可夺人性命。
「公主,是不是太子亲自出马这不重要,西狄想要的仅仅是一个结果,这玉伽关。」他的声音凉了凉,染上了些许怜悯的意味,「您怕是朝廷中混得不好,虽权倾朝野,然也处处提防手下人,故而才自取下策来这边疆赌一把,赌民心赌军功,是么?」
「岑将军到底降没降,其实你心里也没个底对么?」
然后他又很可悲的语气说道:「公主,您其实从未相信任何人。」
这倒被他说对了。
吸引的本质是价值交换。我虽在南芜朝中手下众多,殿内近半数大臣皆私下归顺于我,然也不过是那些纠葛的利益关系,若一日我失势,他们必然如墙头草般翻了脸色又在我头上踩上一脚。
虽说岑晟明面上坚定我的立场,但这也不过是架在他将军府上下几千口人可以温饱无忧的基础上,若是有人开了更大的筹码,也说不准他心里家与国孰重孰轻了。
相信谁?这乱世风雨飘摇,人人皆自顾不得,又如何让我掏心掏肺放下防备去相信谁呢?
「张丞相是聪明人,此处就你我二人,有什么话不妨开门见山直接说了。」我收了剑,敛起神色定定地看着他。
「好啊,公主若是明天便率兵回朝,我保准岑将军能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南芜境内,且你化解了一场劳民伤财的纷争,想必边疆百姓皆会记挂住你。」
若是岑晟真的降了,那必然是西狄的座中宾,又怎么会沦为威胁我的筹码?
我的眼皮跳了跳,张御息真是百密一疏啊,居然出了致命的纰漏,若此刻换成秦慕,他或许便不会自相矛盾,拿张御息的事要挟我了。
岑晟是否在他手中,此事还尚未定论。左右,岑晟未降。
我稳住心神,冷笑道:「以一关之地换一寝安宁,以黎民感激涕零来掩盖神鸦社鼓,这番说辞冠冕堂皇,你们北黎的人可真是道貌伟然啊。」
「既如此,那也没有谈的必要了,我一朝身为南黎公主,便会护着南芜疆土直至化为白骨。」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zhufuyu/148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