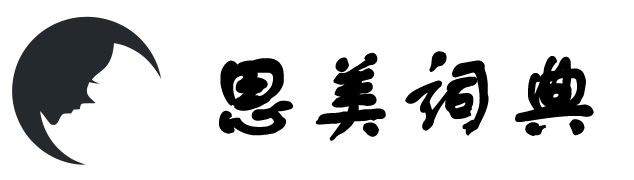第二天,周月又给我发了消息——
「我看到你给江淮打电话的记录了,你已经和他说清楚了吧?他现在精神状态有些不好,一直在喝酒,但没事,我会安抚好他的。」
「孟好好,谢谢你。」
看着那些文字,我回复——
「周月,你挺烂的,你和江淮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刚刚点了发送,猩红的血液就滴到了手机上,跟着第二滴,第三滴,我慌忙抓纸巾去捂鼻子。
提着饭从外面回来的陈琦,看到我的模样,手里的饭掉到了地上,她冲过来一边帮我捂鼻子,一边泪眼婆娑地求我:
「好好,我们去医院治疗吧?我求你了,你别让我这样看着你,什么都不做。」
哎,这么血腥的场面让我的琦琦看到了,她后面会做噩梦的吧?
想到我离开后她难过的样子,我好心疼啊。
我爸留给我的钱,我有在考虑怎么处理。
在知晓江淮的事情前,我本来想的是捐给孤儿院,但知晓他的事情后我就不想捐了,而是选择把钱投到我和陈琦创办的工作室里面。
工作室是我和陈琦的心血,既然都被她发现我的病了,我也该给她留点什么。
做完这一切,我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我七岁时,有人到我家告诉我和我妈:
「江军死了,而且他是个逃兵,这个消息我们不会对外讲,但你们家享受不了烈士家属的待遇。」
知道这消息的那一年我们家仿佛天塌了,我妈怨天尤人地哭了几个月,然后我们家又来人了,是我爸以前的战友来看我们了。
几个叔叔给了我妈一沓钱,说了些安慰的话,但有一个叔叔不一样,他给了我妈一点现金又问我妈要了银行卡号,临走还留了个手机号。
我爸的那些战友们真是雪中送炭,不仅是那些现金给了我们生活支柱,还有一个叔叔每个月会往我妈卡上打五百块钱。
我妈在连续几个月收到钱后就开始天天念叨「好人啊」,还叮嘱我「等你长大一定要还人家恩情」。
在念叨了一段时间后,她就给对方打去了电话。
「恩公,你真是我们家大恩人。」
对方却告诉我妈,他也有个孩子,但他妻子去世了,他太理解这种单亲家庭的苦了,他就是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下我们。
那是我第一次接收到有关孟好好的信息,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个跟我同病相怜的孩子。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妈又拨通了对方电话,还把手机给我让我给那个叔叔拜年,我听着对方讲普通话,其实我那一口乡音讲的很局促。
我拜完年,我妈又把手机拿了过去。
「恩公,都是因为你我们家江淮才能读书,才能活的这么好,您就是江淮的再生父母,要不您收下江淮这个干儿子吧。」
我妈讲的恳切,不顾我愿不愿意,好在对方拒绝了。
挂了电话她又有点担心,给我们打钱的那个人不收我当干儿子,是不是不愿意在资助我们了,毕竟经年累月地资助别人挺考验人的。
可第二年钱没断……
第二年过年,我妈又提认干儿子这事,我还是不想认,好在对方又拒绝了。
挂了电话,我妈又讲,「人家对咱们家这么大恩,这过年怎么也得去给人家拜个年。」
她想的挺好,但她找村里人打听了一圈,去恩公家得坐两天火车,而且一张火车票得 218 块钱,来回得 436 块。
我妈算了算账,436 块钱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又作罢了。
也是,她连借人家手机打个电话都心疼电话费,更何况买那么贵的火车票。
第三年,对方的资助依旧没断。
对方的资助一直没断,只是最开始是五百,我读初三的时候变成了每个月一千。
就这样好多年过去,我连恩公长什么样都不清楚,只能每年过年才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借着嘈杂的音质揣摩对方的形象有多伟岸。
日子久了,我妈仿佛习惯了,对方没按时打钱时她还会打个电话过去催一催,而且她也不对我提报恩还钱的事了。
那时在镇上读初中的我已经懂了礼义廉耻,我妈的做法我挺不齿的。
小时候她教我知恩图报,可我懂事了,她却开始忌讳别人提恩公资助我们家的事,而且不想还钱了。
我们明明有手有脚,能自己赚钱,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的施舍?
我很厌恶我妈这种人,但我拦不住她,她总会背着我去伸手。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97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