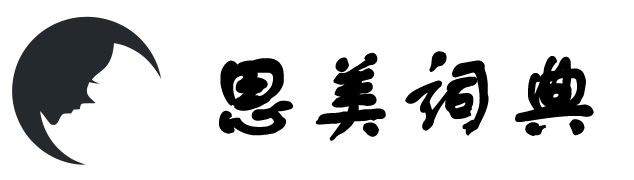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小姑娘刚去世时有个高个女生来过,目测得有一米七吧,我当时见人家长得好看,还拍了照片,本打算给我儿子介绍相亲呢。」
大妈很热情,把照片翻出来给我看。
这不就是……陶然吗?
我惊了。
都不在一个城市的人,陶然怎么可能会跟阿秋认识?
不对不对……
陶然的性格转变得也很奇怪,明明她之前是粘着段洲的,为什么这次回国却一直粘着我?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看完照片把手机还回去后,大妈又特别热情地问我:「姑娘,你结婚了吗,我儿子长得还挺帅的……」
我勉强笑笑,婉拒了大妈的相亲诉求。
浑浑噩噩地下了楼。
其实阿秋葬在哪这件事并不难猜,因为我们说过要葬在一起的。
只是她先走了太多太多步。
那个墓园我找了一个下午,终于在最后一排看到了熟悉的名字:沈秋。
墓碑周围很干净,上面还摆着一些贡品。
一看就是有人常来打扫。
可是阿秋唯一的亲人早就去世,这里还会有谁来?
我小心翼翼摩挲遗照上阿秋的笑容,嘴里念叨着这一年发生的事。
讲了好久,最后还埋怨地说了句,「你恨我就恨我呗,怎么最后还不让我找到你了。」
我在她的墓碑前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登上了回家的旅程。
乘出租车路过段洲的公司大楼时看见里面灯火通明,我没忍住,下了车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总裁办公室。
段洲正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看见我来很诧异。
他还没开口,我就哭着跑过去了。
其实挺奇怪的,知道阿秋去世的时候没哭、看着阿秋的墓碑时没哭,反而现在看到段洲后,哭得撕心裂肺。
就像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熊被隔壁坏孩子「肢解」后我没第一时间哭,但在爸妈下班回来后却抱着他们使劲哭诉。
只是他们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我们工作完已经很累了,你就别在这儿哭闹给我们添堵了。」
然后,就把我一把推开。
为了防止段洲也会推开我,我双腿盘在他的腰上,用力抱住他的脖子。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陶然欺负你了?」
他没见过我这种阵仗,文件也不处理了,有点手忙脚乱的。
我摇摇头,哭着说:「阿秋、阿秋去世了。」
段家选媳妇一向严谨,他们或许在结婚前就查过我的身份背景,应当也是知道阿秋在我生命里的分量。
果然,段洲并不诧异,也没询问阿秋是谁。
只是一味地轻拍我的背,嘴里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个字「乖」、「别哭了」。
就像是没怎么安慰过人。
段洲昂贵的西装被我攥得皱皱巴巴,肩膀处也湿了一大片。
后来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只知道段洲最后提前下班、把哭睡着的我抱回了家。
第二天醒来,我想起来自己昨天晚上大哭特哭的场景,尴尬得不敢睁眼。
其实很奇怪。
明明我觉得和段洲的婚姻名存实亡,明明一个多月前都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可现在好像有点越来越离不开他。
我是个认死理的人。
看中了就是一辈子。
但我一开始以为我看错了,后来才发现不是的。
无论是第一次相亲时恰如其分地照顾不会吃西餐的我,还是明明我从来没去过段洲公司,但第一次去却能畅通无阻地到达总裁办公室,又或者是工作狂的他肯提前下班三个小时,一切都在告诉我说:
好像……段洲也有在悄悄爱我。
他的爱规矩、古板、笨拙,只有偶尔被外界激一下,有了危机感,才肯变得不太规矩。
就像陶然说的那样:我哥啊,很闷骚。
起床后,我俩都默契地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
他怕我伤心,而我在等待着一个确定陶然身份的机会。
我不太清楚陶然知不知道我昨天哭的缘由,于是吃了饭便主动提出带她去临市玩。
陶然茶里茶气地捂住嘴巴,故作惊讶,「啊,可是我刚刚听说哥哥为了陪嫂嫂特地请了一天假呢,这样哥哥会不会不开心啊。」
好的,看样子她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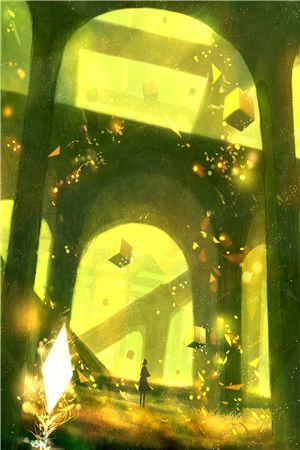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952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