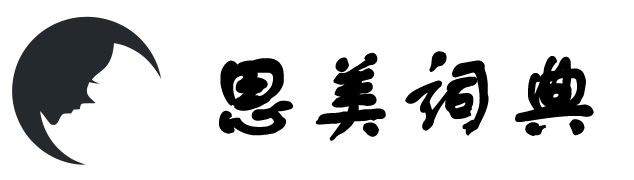时芊也就没再多问了。
像高煦这样流放过来的壮劳力,都要被分配到采石场上工,干最重的活,挣最少的钱,和现代的犯人改造似的。
吃了饭,高煦还没回来,裴夫人便有点着急了,天都这么黑了,还能干什么活?

裴夫人一个劲的往门外看,眼中的担忧十分明显,她夫君和大儿子都死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就是她的命,若是他们出事了,她就算是死了,也无颜面对裴家的列祖列宗。
她的情绪也影响到了裴恒,裴恒开始不安的扭动,眼巴巴的往门外看,大眼睛里满是不安和恐惧。
裴恒今年六岁,本来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可家中突遭变故,流放路上又被吓着了,从来到这里,他就没再说过一句话,一到了晚上更是情绪不稳,如果裴夫人不在,他就会大喊大叫,哭闹不止。
时芊站起来道:“我去门口迎迎他,您哄着小弟先睡。”
裴夫人担忧:“你身子还没好……”
时芊说:“没事,躺了一天,我也活动活动。”
裴夫人只好点头:“锅里热了饭,阿湛回来直接就能吃了。”
时芊看着她们进了屋子,这才舒了口气,回她屋子拿了件衣服穿上,往大门口走去。
今天是十五,月亮像个大圆盘挂在天上,照亮了一方天地。
时芊没敢走太远,就在不远处的路口等着,没等多久,远处摇摇晃晃走来一个人。
等近了,时芊看清楚,正是高煦。
高煦的长相不像大公子那么刚毅英气,他的样貌随了裴夫人,五官偏艳丽,皮肤白皙,比女人漂亮却丝毫不显女气,却又比男人帅气,清冷的月光的洒下来,给他周身度了一层银色,更显的他面如冠玉,一双桃花眼,不笑都自带几分风情,勾人心魄。
此时这双本来艳丽勾人的桃花眼,正直勾勾盯着自己,黑沉沉的眸子蕴含着狂风暴雨,像黑夜中出来觅食的精怪,下一秒就要将人吞食入腹。
时芊被他看得心头一跳。
她想起京城的一句传闻说,烟花八巷的姑娘们加起来都不及裴二公子三分颜色,还有人戏称,若是裴二公子去选花魁,就没有楚诗诗什么事了。
当时时芊还觉得人们夸大其词了,可现在时芊认真的觉得,男人真的可以被称为花魁。
如今裴花魁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盯了时芊一会儿,忽然伸手掐住了时芊的脖子,用力将她按在了树上的。
时芊触不及防的被来了这么一下,只觉后背生疼,眼冒金星,她用手去掰高煦的手,高煦手指冰凉刺骨,像铁钳一样死死的按着她,神情凶狠,一张漂亮的的脸上带着几分狰狞:“不是想死么?不如我成全你如何啊?大嫂……”
他特意拖长了“大嫂”这两个字,声音低沉温柔,明明像情人间的细声喃语,可手上却做着最残忍的事,听的时芊浑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时芊用力掰着他的手,她之前上吊,脖子的伤还没好,如今又被高煦掐着,像只被老鹰抓到的小鸡崽,毫无还手之力,只要高煦再用点力,她就又可以继续做阿飘了。
就在时芊以为要死的时候,裴花魁终于开恩放开了她,时芊毫无形象的跪在地上捂着脖子剧烈咳嗽,高煦则蹲下来,睁着一双含情的桃花眼,关切的看着她。
“大嫂,你没事吧?”他贴心的拿出手帕给她擦了擦嘴角流出来的口水。
时芊就跟被恶鬼盯上一般,躲开高煦的手,愤怒的瞪他。
虽然没有原主的记忆,但是她在裴大婚宴上见过这位二公子曾经的模样,当时的他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和一群公子哥们打闹着,挡在大哥面前替他挡酒。
从裴家事发到现在也才短短几个月,高煦瘦了一大圈,风一吹就能倒下似的,一头墨发只用根木棍随意的绾着,虽然面容没有多大变化,却再没了从前少年人的纯真模样。
裴二公子死了,死在了京城十月的荒秋中。
时芊有一瞬间的怀疑,眼前这个根本不是高煦,而是被什么恶鬼附身了。
高煦懒洋洋站起来,用帕子擦了擦手,声音依旧温和,语气却透着说不出阴冷:“大嫂,我们该回去了,晚了,娘该担心了。”
时芊站起来,捂着脖子不发一言,只是死死的盯着高煦。
高煦扯着嘴角冷笑一声,警告:“没有下一次。”
这是他对时芊最后的警告。
若不是因为流放犯人自裁是大罪,会连累裴家,高煦绝对不会花费哪怕半点心思去救她。如果再有下一次,他不介意亲自送她上路。
宁州苦寒,每天都要死人的!
时芊艰难的滚出这个字,只觉得喉咙剧痛,浑身无力。
听到她要喝水,裴夫人脸上瞬间带了笑,忙去给她倒水。
时芊忍着痛喝了一大杯水,这才感觉好了一些。
裴夫人试探着问:“阿真饿了么?我煮了粥,要不要吃点的?”
时芊确实饥肠辘辘,便点点头。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wenyi/1371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