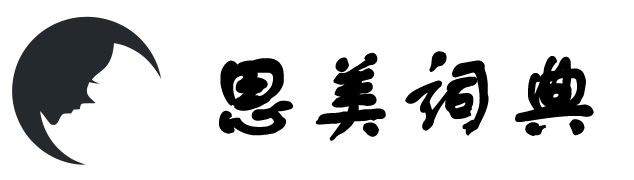我醒过来的时候,人在医院,洗了胃捡回一条命。
是村长救了我。
爸妈是奔着求死去的,毒药的摄入量很大。村长到的时候,两人已经不行了。
我吐了一些出来,保住了小命。
白雪食量小,也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一直昏迷不醒。
爸妈没有亲戚,出院后,我们俩就住进了村长家。
他们夫妻年过半百,但没有孩子,就收留了我们。
李叔和李婶是极好的人,对我格外照顾,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关爱。
是他们帮助我,从失去家人的无助和悲痛中恢复过来。
父母的葬礼是他们帮忙操办的,白雪还未苏醒,也一直是李婶在细心照料着。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从我家找出了我藏起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替我交了学费,还亲自送我去了学校。
那会儿其实已经开学了,我因为住院没赶上报到,他们早早就替我向学校请了假。
我顺利踏进大学校园的那一天,李叔李婶站在学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去,就像那些普通的父母一样。
十月天气转凉了,秋风拂过脸颊,却很暖很暖。
以前为了赶回家帮妈妈照顾妹妹,我整个高中都是走读的。
现在我的学校在市里,回村需要半天时间,李叔李婶给我办了住校。
白雪现在昏迷着,不需要像从前那样随时守在身边。
我终于重获自由,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活。
怎么来形容当时的感觉呢?
就好像快溺死在海里的时候,突然被人捞了出来,大口大口的空气灌入肺里。
没错,是重生的感觉啊。
曾经那些可怕的记忆在我脑中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充实的学习生活,和久违的轻松感。
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白雪醒过来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伤了李叔和李婶。
我收到消息赶回家的时候,妹妹已经被绑起来了,李叔的左眼瘀青一片,李婶的额头肿了个大包。
他们本不用承受这些的。
愧疚感让我无地自容。
我想带着妹妹离开,可我们又能去哪呢?
李叔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怕我自责,递给我一个剥好的鸡蛋,说:「去给你李婶揉揉。」
李婶也轻声安慰我:「俺们俩没事,都是粗人,皮糙肉厚的。」
他们说把我当成了亲生的孩子,让我别多想。
我哇地一下哭出了声,我好想留在他们身边。
人这种动物,最不怕吃苦,怕就怕苦尽甘来之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幻梦一场。
尝到甜头之后,就真的很难再回去了。
妹妹又被套上了铁链,我只要学校没课,就赶回来守着她。
学期最后一天我回来得早,不小心听到了李叔和李婶的谈话。
李叔抽着烟,一脸愁容,「要不给白雪找个精神病院?」
李婶在一旁按着计算器,皱着眉头,「得请看护,要花不少钱的。政府给的补助根本不够,咱还要供小洁读书呢。」
李叔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小洁是个好孩子,就是被这个妹妹拖累惨了。」
「谁让你当时两个都救的?」
「有其他人在场看着的呀。」
「那以后到底咋办?」
…………
毕竟不是亲生父母,天天照顾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一定已经到极限了吧。
我走进家门,装作无事发生,默默进了妹妹房间。
「真羡慕你,什么都不懂。」我扯出一丝苦涩的笑。
白雪又犯病了,狂暴地看着我,闹得比平常更凶了。
一直到深夜,都不曾停歇。
我听见李叔、李婶的房门开关了许多次,一定是睡不好。
寂静的黑夜里,铁链哐当哐当的声音突然让我觉得无比烦躁,这根链条就像锁在了我身上,怎么都无法挣脱。
如果没有妹妹,那该有多好。
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
等妹妹睡着后,我走到她身边,直愣愣地盯着她看,就像曾经她砍我的那个雨夜一样。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一旁的枕头,捂住了妹妹的脸,闭上眼睛用力按了下去。
没有遭到抵抗,我觉得有些奇怪,睁开眼,看见妹妹的双手紧紧拽着床单。
她没发出一点声响,就像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她现在,是清醒的吗?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慌忙移开枕头。
妹妹的手跟着放松了,但眼睛仍然闭着,就像还在睡梦中一样。
我想道歉,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悲剧的种子,就是这时候播下的吧。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shuoshuo/177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