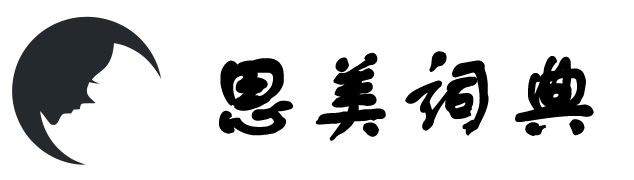江以南带我回了自己的公寓。
出乎我意料,他并没有很急,等我磨蹭了半天裹着浴巾出来,只看了我一眼就进了浴室,接着里面响起花洒的水声,只是玻璃门上没有起雾,或许用的是冷水。
我想了想,去了他的书房。
刚在一起的时候,江以南的温柔总让我想挑战他的底线。
他对我的感情过于小心翼翼,半个月了连手都不敢牵,还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把抓着他不放才算是碰着了,到谢幕时他掌心都是汗,红着脸小声解释是电影院暖气开太足了。
我喜欢逼他做他本来不会做的事。
比如在凌晨空旷的大街上接吻,又比如把车停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将手伸进他衣摆下直弄到他面红耳赤为止。
江以南一直是被动的一方。
我其实没多少耐心,有了几次外面抽纸巾的经历以后我就带他回家了。
「热水这边,沐浴露这个。」我靠着玻璃门问,「没问题吧,不行的话姐姐可以陪你一起洗。」
他进门以后强装的淡定在我这句话中土崩瓦解,把我往外推:「我可以。」
我裹着浴巾,他推我时碰到我的背,又是一阵脸红。我望着浴房里的剪影心说这就不行了,那你今天晚上可别想睡了。
江以南洗完澡出来,居然还老老实实穿了睡衣,坐在床边跟个小媳妇似的。
我觉得很好笑,勾着他的下巴让他看我。
我身上是一条真丝吊带裙,里面不着寸缕,一俯身,他的视线正好对在我身前,只一瞬他便移开了眼睛。
「过来。」
我拉着他往外走,他不明所以,傻乎乎被我带到了书房。
我很喜欢看书,书房里有一张巨大的书桌。
书桌么,除了看书,其实还有点别的用处。
我引他到桌边,坐上桌沿开始动作。
江以南有点反应不过来,我不客气地摸上他的腹肌:「你不是说要和我从图书馆开始么?图书馆是公共场合,姐姐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吧。」
「在,在这里——」
他的耳朵爆红,在书房暖色灯光下像鸽子血似的,我忍不住咬了他一口:「听话。」
他伸手搂住我,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我贴着他的脸咬唇问他:「想不想,嗯?」
他不答,手上力道加重。
「想叫姐姐。」我说。
他只喊过我一次姐姐,就在我醉酒的那次,后来不管我怎么哄他都不喊了,好像很介意自己比我小这件事。
但我一向是长着反骨的,专爱逼他做他不乐意的事儿。
我手上动作。
他快到极限了,红着眼看我。
「叫姐姐。」我微微俯身,让他触到我。
「……」
江以南探身来吻我眼角,用求饶的目光望着我。
我不为所动:「叫姐姐。」
……
最后江以南还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下喊了一声姐姐。
可见人的底线就是用来打破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那晚他红着眼喊我姐姐,几度沉沦,像被艳鬼拉进地狱的纯白神灵。
……
我的思绪被江以南的吻打断。
他将手掌覆在我眼上,轻吻我的脸颊。
「以南?」
「姐姐……」他手指温柔地像在触碰瓷釉,「姐姐。」
我有些痒,扭着腰躲他,被他框在方寸之间不得动弹。
我躺倒在床上,浴巾散开,江以南的吻温柔的落下,从耳后蔓延至心口。
我听见他问:「姐姐,你有没有心的?」
有没有心。
怪不得要捂着我的眼睛。
面对我他根本无法问出这句话,这话看似在在问我,其实诛的是他自己的心。
他怕了。
他曾说会让我爱上他,可是他打了退堂鼓。
因为我身边层出不穷的男人实在太多,昨天是易泽,今天是何许,明天冒出一个秦牧也,每一个都让他无力。
很多人陷入爱情以后都会产生自我怀疑,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这件事几乎能把人折磨死,要是换了平时我愿意哄他。
可今天我有些累了。
江以南见我不说话,几不可查地叹了口气,想要松开我。
我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将他拉了回来,吻住他的唇,「我就在这里。」
「什么?」
我重复一遍:「我就在这里。」
他眼中透着迷茫,可我不想让他再有思考的时间,翻身将他压在身下,轻吻他的喉结:
「来我公司吧,陪着我。」
8
江以南来我公司我没给他走后门,他的专业对口成绩也好,入职是意料之中。
工作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反而变少了,他作为新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也不愿意来办公室找我,怕别人以为我们是那种关系——虽然我们确实是。
「程总,有人给你送礼物哎。」
我的助理给我带来一个盒子,上面挂了张卡片,写着「一会儿见」。
「好浪漫呀!马上要见面了还给你送东西。」小助理满脸八卦表情,「是谁啊?」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人的脸,随即摇头,应该不是他,他都出国一年了。
我拆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瓶香水。
银色山泉。
这是我们最近正在推动合作的一个香水牌子,里面有一个调子,是白松香。
我挑眉,问:「跟他们公司的合作推进了?」
「哦对,」小助理一拍脑门,「程总,这次格外顺利,我本来以为还要再拉锯几次的,没想到他们那边直接定了我们公司合作。说是已经有了代言人,要马上拍广告了。」
代言人……怪不得秦牧也说我逃不掉。
既然要合作,我这个老板怎么可能躲着他呢。
「对了程总,刚才小蔡告诉我何总要来——」
小蔡是何许的秘书,我正疑惑他为什么忽然要来我这儿,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秦牧也今天穿的随意,很像刚进校园的大学生,仿佛已经来找过我无数次一样熟门熟路地走进来,手搭上我的椅背,俯身揉我的头:「发型不错。」
我拍开他:「不错也被你揉乱了。」
小助理眼睛都瞪大了,我才想起来她是秦牧也的狂热粉,在她「老板你认识秦牧也居然不告诉我太过分了」的哀怨眼神中,我扶额,对她挥挥手:「你先出去,不要让人进来。」
「不要让谁进来?」小助理刚拉开门,又是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
何许冷着脸迈进来,见秦牧也在我身旁,眼睛微眯,直接把他当空气,朝我伸手:「小鹿,中午了,一起吃饭吧。」
来的这么快,估计是听到秦牧也要跟我合作的消息以后立马赶来了。
秦牧也把他的手挡住:「先来后到懂不懂?」
「要说先来后到,那也应该是我。」我转头一看,感觉头要炸了,夭寿,居然忘记今天约了江以南一起吃午饭。
江以南拿着两个便当,倚在门边,身后是绝望的小助理:「程总我……」
嗯,没事,我理解你,你一个都拦不住。
「姐姐这里人好多,我只做了两个便当。」江以南将便当放在我面前,又给我倒了杯水,亲昵地刮刮我鼻梁,「怎么总要我提醒你喝水?」
我:「……」
完了,连江以南都不打算放过我了,看着贴心,其实笑里藏刀。
温柔刀,刀刀要人命。
秦牧也看江以南一眼,话却是对何许说的:「需要别人来照顾小程,要你何用?」
何许松松领口:「比一点忙都帮不上的人强多了。」
秦牧也眼角一跳,上前一步冷笑道:「你难道帮上忙了?你当年藏着什么龌龊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你也配娶她?」
得,开始相互诛心了。
「不管怎样,她现在是何夫人都是既成事实。」何许玩着领带,「小鹿,你给我买的领带我很喜欢,一会儿陪我再去配几条?」
「她没空。」江以南淡声打断,「姐姐,该吃饭了。」
「小程,我们得讨论一下广告拍摄问题。」秦牧也握住我的肩膀,「去我那儿。」
「拍广告你找摄影师去。」何许开始吩咐司机去楼下待命,「我和程总要去泰银。」
「小程高中的时候可喜欢拍照了,和我聊聊拍摄想法怎么了?哦不好意思,我忘了那个时候小程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喜好呢。」
何许指节轻敲桌面:「秦牧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要脸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人的脸皮有厚度?」
我在夹缝中艰难出声:「那什么,我……」
「你闭嘴。」男人们异口同声。
我:「……」
好嘛,我今天是没有自主选择权了。
不知道等下我能不能有机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他们三个站我旁边各成一角,阴阳怪气了好一会儿,最后把炮火转向了我:「你想去哪儿?」
我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一一扫过,发现他们此刻的表情大有「你要是敢选另外两个我就死给你看」的意思,幽幽叹了口气。
天真,成年人做什么选择?
我拿出手机想给易泽打电话,让他们三个自己过去吧。
电话还没拨出去,我看见一个许久未见的号码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贺呈。
我当即把手机往心口一贴,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借过,我去下洗手间。」
9
我带上耳机走出办公室,将背后的三道视线隔绝在门后,才按了接听。
「……」
「现在有空么?」没有寒暄也没有解释,贺呈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沙哑。
我下意识点头,然后才想起来他看不见:「有,我来找你?」
「好。」
我在楼下买了一份冰糖雪梨,然后驱车往贺呈家去。
贺呈和我见面,永远是在他家里,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拉上。
这样的空间会让人感到压抑,但也会给予人安全感。
尤其是对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来说,一个密闭的房子能让人更加安心,比如九年前的我。
他家在老别墅区,我小时候常来,因为我爸当时跟何家关系很好,我每年会来这里拜年,拜年的时候就会看见何许。
何许总是安分地站在何老爷子身边,对我们露出彬彬有礼的笑容。
不过后来他们搬家了。
程家出事后,何家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何老爷子嫌这个地段不吉利,就把房子给卖了。
辗转几次后,这房子落入了贺呈手中。
门是开着的,我敲敲门走进去,径直上了二楼。
二楼有一个巨大的圆厅,外圈围着整排的书架,上面很多书是贺呈搬进来后才放上去的,那些书曾陪伴我走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留声机里放着低沉的萨克斯独奏,古老的水晶灯无法将大厅完全照亮,暖黄的光温柔地洒下,为坐在地毯上看书的那个男人镀上一层柔和的滤镜。
他穿了一件黑色毛衣,像一只在白色毛绒地毯上打盹的黑猫。
贺呈听见我的脚步声,抬头冲我笑了笑。
他的眉眼很深邃,平时看人会显得有些深沉,唯有垂眼看书时会露出放松的神情,这会儿看我的眼神很平和,想来看的书应该挺合心意。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把冰糖雪梨递给他。
他舀了一勺:「昨天。」
「怎么不告诉我?」
「你忙。」他把碗底的糖水浇在雪梨上,「程大小姐身边那么多人,把时间花在我身上就浪费了。」
我懒得理会他话里的调侃,问他:「秦牧也和我公司的合作是不是你干的?」
他几口吃完了雪梨,拿纸巾擦了擦嘴,这才慢条斯理道:「稍稍推动了一下进度,本来也是属意于他的,再者我和秦家最近也有个合作,就当卖秦总一个小人情了。」
我无奈:「你没必要把他扯进来。」
他朝我伸出手,我和他对视,他温和地望着我,几秒后我只好将手放在他掌心。明明我站着他坐着,他却将主动权牢牢把控,这是他的习惯。
贺呈牵着我坐下,替我整理了一下头发:「给何许找点事做,他的注意力分散些比较好。」
我心道你都把他的身世透给何老爷子了难道还不够么?却也知道他决定的事无法更改,于是换了个话题:「你吃饭了么,我有点饿了。」
「想吃什么?厨师不在,我给你做。」
「炸酱面吧。」
第一次见面时贺呈为我做过一碗炸酱面。
九年前,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医院传来我父亲身死的消息。
他进 ICU 不过两天就撑不住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时间,等我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时,人已经在殡仪馆了。
程家各系亲戚吵成一团,公司里的股东也闹的不行,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我刚刚失去了父亲,有对我冷嘲热讽的,也有对我极尽巴结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想趁乱分一杯羹。
我对公司的事其实不甚了解,但何家在程家是占了股份的,很多人就把主意打到了何家身上,何许那时已经开始管事了,他是我爸钦定的女婿,很长一段时间都和我绑定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以为何家会对程家施以援手。
可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对当时的何家来说,帮助程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公司董事给何许打过电话,第三次才有人接。
电话那头他问:「出了这么大的事,程鹿清为什么不来见我?」
我爸生死未卜,公司乱成一团,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见他。
他在等我去见他,但他不会自己提出来。
何许总是喜欢这些弯弯绕绕,程家有意与何家联姻,所以他每年都送我许多礼物,在我生日那天空出时间来见我,有礼,规矩,一举一动都符合我爸的期许,至于我喜不喜欢他,那不在他考虑的范畴内。
我和秦牧也在一起的第一年,我本来想和他一起过生日,可我爸非说约了何许来家里做客,闹的我很不高兴,全程面无表情,气的我爸直瞪我。
何许就笑着和我爸说:「小鹿还小,没有在社会里磨砺过,有脾气很正常,玫瑰都是带刺的。」
那时他看我的眼神,宽容又冷漠。
我是一朵养在温室的玫瑰,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要被暴雨折弯了腰,便不得不屈服于他的保护。
他是这样想的。
那天何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可以来何家跟何许商量转移股权的事,最后提及何许的喜好:「来的时候带瓶豆奶吧,他爱喝这个。」
他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老了,不管事了,还是得看何许怎么想,提点我的样子像极了为我考虑的长辈。
可他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得意,得意我无依无靠,得意何许高高在上,得意曾经有意联姻的程何二家,现在要靠程家大小姐来讨好何家公子度过难关。
何老爷子希望我做一只乖乖听话的金丝雀,交出程家的一切,然后作为精致的展览品成列在何家的展柜里。
商人重利,一切皆可算计。这是何老爷子借程家磨难为何许上的一课。
但我没有去何家。
何许对我征服欲来自我十年如一日的冷淡,他有过许多女人,那些女人或求色或求财,唯有我,眼中从来没有他,也从不向他求什么。
他对我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
可他追求的人是不存在的,他想要女人高傲,又想要女人臣服,他天生带着征服欲,又将对他动心的女人弃之如履,这是死循环。
若我没有坚持,现在也不过是他的过客罢了。
我爸火化后,早就不耐烦的人们散去,留我一人坐在殡仪馆旁边的台阶上发呆。
我抱着他的骨灰盒,从正午坐到日渐西斜,天边燃起火烧云,下班的工作人员感叹:「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想的居然是,在作文里,这是对比的一种写法,用相反的天气来衬托主人公的内心情感。
我用语文老师的语气问自己,那么此刻主人公内心想的是什么呢?是她爸临死前交代的遗言:「和江柔葬一起」。
我被自己逗笑了,心说这他妈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去你妈的死老头,把我妈气死了还要跟你姘头合葬,你想都别想。
夕阳烧的我脸上一阵热意,泪水蒸发后脸因干燥而刺痛,我想站起来,可腿麻了,挣扎了半天干脆放弃抵抗,自暴自弃地等神经恢复。
这时有人挡住了光线,一片黑色风衣的衣摆垂在我眼前:「程鹿清。」
我抬头,逆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血红色的落日勾勒出他的轮廓,他有一个好看的下巴。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问了一句:「有烟么?」
他从口袋里拿出烟递给我,又挡着风替我点了火。
我叼着烟猛吸了一口,差点呛得咬不住。
他轻声笑了,衣摆一撩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慢慢来。」
我咳出了眼泪,不服输地又吸了一口,然后缓缓的吐出来,面前烟雾缭绕,忽然就觉得没那么难受了。
「挺好,有成为烟鬼的潜质。」他赞了一句。
我转头看他,这个男人有一张立体的脸,眉弓高,眼窝深,鼻子虽然挺但并不粗糙,显得有些俊秀,中和了立体眉眼的雕塑感。
他的下巴带点方,上面有零星胡茬,但并不影响他的整体气质,反而很有男人味。
看见他脸的瞬间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何许像他妈妈,长相偏阴柔,而何老爷子年轻时也算是一代青年才俊,据说他的大儿子,很像他。
男人见我看着他的脸不动,笑了笑自我介绍道:「我是贺呈。」
他是改了母姓的,他的母亲本就是个女强人,离了婚仍有生活和后盾,而我妈……嫁人以后完全丧失了自我,沉溺在过去无法自拔,不能接受我爸找小三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是自怨自艾,到最后含恨离去。
可笑的是我爸三个月后就把小三带回家了,那个江柔,看着柔柔弱弱,其实主意大的很,把我爸唬的神魂颠倒,往公司塞了一堆人,结果闹出了问题,让人卷钱跑了,我爸和她一起去追,要不是这样也不会出车祸。江柔当场死亡,我爸……过了几天也去陪她了。
我低头将情绪压住,冷着眼与贺呈对视,可能过了几分钟,也可能只是几秒,他忽然笑了。
他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包湿巾,抽出一张给我:「聊聊?」
我站起来,走下台阶:「送我去海边。」
他没问我做什么,开车带我往沿海公路去了,还很体贴地敞着篷,以便海风可以及时吹干我的眼泪。
我把骨灰都撒进了海里。
连同过去一起。
从那一刻起,程鹿清就是独身一人了。
「我饿了。」
我对贺呈说。
他带我回了临时住处,卷起袖子开始切葱:「炸酱面吃不吃?」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为了报复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择手段,却又有耐心陪我一个毫无根基的倒霉鬼浪费时间。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亲自下厨,他煮面时充满了烟火气,可解了围裙后办公的眼神又很锋利,察觉到我在看他,贺呈合上电脑为我倒了杯水,轻轻揉了揉我的发顶:「一切都有代价,你以后会懂。」
有了贺呈的帮忙,程家总算挺住了,虽然伤了点元气,但不至于被人吃干抹净。
「程鹿清,你太弱了。」贺呈替我稳住公司后说。
跟贺呈打交道其实很轻松,因为我们都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直来直往,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他对我很严厉,请了老师来辅导我功课,高考后更是直接带着我熟悉公司事务,手把手教我一切该学的。
他会用最平淡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问题,让我改文件改两个通宵,也会细心地察觉到我的体虚给我配中药调理,送我绝版的旧书。
他教我为人处事,教我长袖善舞,教我掩藏情绪,每次我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带我去海边看星星。
我们会脱了鞋光脚踩在沙滩上,感受海水的涨落,听风拂过海鸥翅膀的声音。
后来他将何家别墅买下来了,我往书架上添了不少书,我们就鲜少再出门看星星了。
自然的广袤星空洗涤人心,而浩瀚书海则给人沉静的力量。
公司事忙,偶有空闲时光,我们便会在圆厅里看书,我手边是咖啡,他手边是白水,手里拿本书,一天无言。
贺呈用五年时间,将我变成了一个和他很像的人。
我们用理智将自己牢牢锁住,情绪藏于内,精致且漠然。
然后我嫁给了何许。
带着程家做嫁妆,嫁给了何许。
何老爷子对我很满意。
贺呈也很满意。
后来他就很少再联系我了,他的生意做到了国外,只偶尔同我在电话里聊聊,谈及的也多是最近新看了一个画展或淘到一张老唱片。除非我问他,否则他轻易不会置喙我的公司管理。
去年他告诉我,他妈妈去世了。
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快见到他了。
贺呈将面端到我面前,手臂自然地搭在我背后的沙发上,我转头去看他。
岁月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有的只是时间的沉淀,他这样稳重又自持的男人,其实很讨小姑娘喜欢。
我在他身边的那几年,有数不尽的莺莺燕燕往他身上扑,他从不带女人回家过夜,但有一次一个相处了两个月的姑娘上门找了我,她问我拿什么迷魂汤蛊了贺呈,居然能住在他的房子里。
我给贺呈打电话,他甚至没有亲自到场,只派了两个保镖将那姑娘架走了。
那天晚上贺呈带回一张唱片,问我:「跳舞么?」
他对于跳舞这件事有很强的仪式感,特意换了西装。
我那时已经出席过很多酒会,他给我买了一整个衣柜的礼服,我挑了件黑色露背裙,行走间摇曳生姿。
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神暗了暗,随后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一手牵过我,一手轻扶我的腰肢。
那是一首安静的曲子,我们只小步地在圆厅中进退,我穿了高跟鞋,正好能将下巴放在他肩膀上。
我们沉默至一舞终了, 我抬起头看他,鼻尖只离他一指的距离,呼吸都能相互缠绕。
有人说,男女对视一分钟以上,很容易出事。
贺呈的眼眸像墨玉般温润却又时时透着悲悯,当他望着一个人时,对方很容易产生自惭形秽的想法,但我那时胆子很大,坚定不移地望着他,一定要等他的反应。
「程鹿清。」
他其实很少笑,但面对我时,却会习惯性牵起嘴角,连带着眼睛也染上笑意。
最后他打破了那一指的距离,抬起下巴,凉薄的唇在我额头上短暂停留了一秒。
若不是他的胡茬刺到了我,我几乎要以为那只是窗外漏进的风。
吃完面我去厨房把碗洗了,然后回到贺呈身边。
难得安宁。
我们就这样静坐,直到窗外响起一声鸟鸣,贺呈起身拉开窗帘,已至黄昏,透过落地窗倾斜进来,他从书架上取出一张黑胶唱片放在留声机上。
前奏响起,是 Careless Whisper。
转身向我伸出手,微微躬身:「跳舞么?」
我仍将下巴搭在贺呈肩膀上。
进退间他安抚地捏住我的后颈,「和从前一样。」
我握紧他的手以做回应。
一样么?不一样了。
我只是习惯了在他面前示弱,看他的眼神中永远带着依赖。
「你们合开的公司财政上有个大窟窿。」他说。
何家的动态一向是他最关心的。
我点头:「我知道。」
他笑:「他想要你折服,可我更喜欢你傲气。」
「他不会如愿。」
「你想好怎么处理了?」
我闭上眼,少年麋鹿般的眼睛一闪而过。
「很早之前,就想好了。」
江以南带我回了自己的公寓。
出乎我意料,他并没有很急,等我磨蹭了半天裹着浴巾出来,只看了我一眼就进了浴室,接着里面响起花洒的水声,只是玻璃门上没有起雾,或许用的是冷水。
我想了想,去了他的书房。
刚在一起的时候,江以南的温柔总让我想挑战他的底线。
他对我的感情过于小心翼翼,半个月了连手都不敢牵,还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把抓着他不放才算是碰着了,到谢幕时他掌心都是汗,红着脸小声解释是电影院暖气开太足了。
我喜欢逼他做他本来不会做的事。
比如在凌晨空旷的大街上接吻,又比如把车停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将手伸进他衣摆下直弄到他面红耳赤为止。
江以南一直是被动的一方。
我其实没多少耐心,有了几次外面抽纸巾的经历以后我就带他回家了。
「热水这边,沐浴露这个。」我靠着玻璃门问,「没问题吧,不行的话姐姐可以陪你一起洗。」
他进门以后强装的淡定在我这句话中土崩瓦解,把我往外推:「我可以。」
我裹着浴巾,他推我时碰到我的背,又是一阵脸红。我望着浴房里的剪影心说这就不行了,那你今天晚上可别想睡了。
江以南洗完澡出来,居然还老老实实穿了睡衣,坐在床边跟个小媳妇似的。
我觉得很好笑,勾着他的下巴让他看我。
我身上是一条真丝吊带裙,里面不着寸缕,一俯身,他的视线正好对在我身前,只一瞬他便移开了眼睛。
「过来。」
我拉着他往外走,他不明所以,傻乎乎被我带到了书房。
我很喜欢看书,书房里有一张巨大的书桌。
书桌么,除了看书,其实还有点别的用处。
我引他到桌边,坐上桌沿开始动作。
江以南有点反应不过来,我不客气地摸上他的腹肌:「你不是说要和我从图书馆开始么?图书馆是公共场合,姐姐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吧。」
「在,在这里——」
他的耳朵爆红,在书房暖色灯光下像鸽子血似的,我忍不住咬了他一口:「听话。」
他伸手搂住我,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我贴着他的脸咬唇问他:「想不想,嗯?」
他不答,手上力道加重。
「想叫姐姐。」我说。
他只喊过我一次姐姐,就在我醉酒的那次,后来不管我怎么哄他都不喊了,好像很介意自己比我小这件事。
但我一向是长着反骨的,专爱逼他做他不乐意的事儿。
我手上动作。
他快到极限了,红着眼看我。
「叫姐姐。」我微微俯身,让他触到我。
「……」
江以南探身来吻我眼角,用求饶的目光望着我。
我不为所动:「叫姐姐。」
……
最后江以南还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下喊了一声姐姐。
可见人的底线就是用来打破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那晚他红着眼喊我姐姐,几度沉沦,像被艳鬼拉进地狱的纯白神灵。
……
我的思绪被江以南的吻打断。
他将手掌覆在我眼上,轻吻我的脸颊。
「以南?」
「姐姐……」他手指温柔地像在触碰瓷釉,「姐姐。」
我有些痒,扭着腰躲他,被他框在方寸之间不得动弹。
我躺倒在床上,浴巾散开,江以南的吻温柔的落下,从耳后蔓延至心口。
我听见他问:「姐姐,你有没有心的?」
有没有心。
怪不得要捂着我的眼睛。
面对我他根本无法问出这句话,这话看似在在问我,其实诛的是他自己的心。
他怕了。
他曾说会让我爱上他,可是他打了退堂鼓。
因为我身边层出不穷的男人实在太多,昨天是易泽,今天是何许,明天冒出一个秦牧也,每一个都让他无力。
很多人陷入爱情以后都会产生自我怀疑,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这件事几乎能把人折磨死,要是换了平时我愿意哄他。
可今天我有些累了。
江以南见我不说话,几不可查地叹了口气,想要松开我。
我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将他拉了回来,吻住他的唇,「我就在这里。」
「什么?」
我重复一遍:「我就在这里。」
他眼中透着迷茫,可我不想让他再有思考的时间,翻身将他压在身下,轻吻他的喉结:
「来我公司吧,陪着我。」
8
江以南来我公司我没给他走后门,他的专业对口成绩也好,入职是意料之中。
工作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反而变少了,他作为新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也不愿意来办公室找我,怕别人以为我们是那种关系——虽然我们确实是。
「程总,有人给你送礼物哎。」
我的助理给我带来一个盒子,上面挂了张卡片,写着「一会儿见」。
「好浪漫呀!马上要见面了还给你送东西。」小助理满脸八卦表情,「是谁啊?」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人的脸,随即摇头,应该不是他,他都出国一年了。
我拆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瓶香水。
银色山泉。
这是我们最近正在推动合作的一个香水牌子,里面有一个调子,是白松香。
我挑眉,问:「跟他们公司的合作推进了?」
「哦对,」小助理一拍脑门,「程总,这次格外顺利,我本来以为还要再拉锯几次的,没想到他们那边直接定了我们公司合作。说是已经有了代言人,要马上拍广告了。」
代言人……怪不得秦牧也说我逃不掉。
既然要合作,我这个老板怎么可能躲着他呢。
「对了程总,刚才小蔡告诉我何总要来——」
小蔡是何许的秘书,我正疑惑他为什么忽然要来我这儿,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秦牧也今天穿的随意,很像刚进校园的大学生,仿佛已经来找过我无数次一样熟门熟路地走进来,手搭上我的椅背,俯身揉我的头:「发型不错。」
我拍开他:「不错也被你揉乱了。」
小助理眼睛都瞪大了,我才想起来她是秦牧也的狂热粉,在她「老板你认识秦牧也居然不告诉我太过分了」的哀怨眼神中,我扶额,对她挥挥手:「你先出去,不要让人进来。」
「不要让谁进来?」小助理刚拉开门,又是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
何许冷着脸迈进来,见秦牧也在我身旁,眼睛微眯,直接把他当空气,朝我伸手:「小鹿,中午了,一起吃饭吧。」
来的这么快,估计是听到秦牧也要跟我合作的消息以后立马赶来了。
秦牧也把他的手挡住:「先来后到懂不懂?」
「要说先来后到,那也应该是我。」我转头一看,感觉头要炸了,夭寿,居然忘记今天约了江以南一起吃午饭。
江以南拿着两个便当,倚在门边,身后是绝望的小助理:「程总我……」
嗯,没事,我理解你,你一个都拦不住。
「姐姐这里人好多,我只做了两个便当。」江以南将便当放在我面前,又给我倒了杯水,亲昵地刮刮我鼻梁,「怎么总要我提醒你喝水?」
我:「……」
完了,连江以南都不打算放过我了,看着贴心,其实笑里藏刀。
温柔刀,刀刀要人命。
秦牧也看江以南一眼,话却是对何许说的:「需要别人来照顾小程,要你何用?」
何许松松领口:「比一点忙都帮不上的人强多了。」
秦牧也眼角一跳,上前一步冷笑道:「你难道帮上忙了?你当年藏着什么龌龊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你也配娶她?」
得,开始相互诛心了。
「不管怎样,她现在是何夫人都是既成事实。」何许玩着领带,「小鹿,你给我买的领带我很喜欢,一会儿陪我再去配几条?」
「她没空。」江以南淡声打断,「姐姐,该吃饭了。」
「小程,我们得讨论一下广告拍摄问题。」秦牧也握住我的肩膀,「去我那儿。」
「拍广告你找摄影师去。」何许开始吩咐司机去楼下待命,「我和程总要去泰银。」
「小程高中的时候可喜欢拍照了,和我聊聊拍摄想法怎么了?哦不好意思,我忘了那个时候小程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喜好呢。」
何许指节轻敲桌面:「秦牧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要脸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人的脸皮有厚度?」
我在夹缝中艰难出声:「那什么,我……」
「你闭嘴。」男人们异口同声。
我:「……」
好嘛,我今天是没有自主选择权了。
不知道等下我能不能有机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他们三个站我旁边各成一角,阴阳怪气了好一会儿,最后把炮火转向了我:「你想去哪儿?」
我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一一扫过,发现他们此刻的表情大有「你要是敢选另外两个我就死给你看」的意思,幽幽叹了口气。
天真,成年人做什么选择?
我拿出手机想给易泽打电话,让他们三个自己过去吧。
电话还没拨出去,我看见一个许久未见的号码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贺呈。
我当即把手机往心口一贴,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借过,我去下洗手间。」
9
我带上耳机走出办公室,将背后的三道视线隔绝在门后,才按了接听。
「……」
「现在有空么?」没有寒暄也没有解释,贺呈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沙哑。
我下意识点头,然后才想起来他看不见:「有,我来找你?」
「好。」
我在楼下买了一份冰糖雪梨,然后驱车往贺呈家去。
贺呈和我见面,永远是在他家里,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拉上。
这样的空间会让人感到压抑,但也会给予人安全感。
尤其是对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来说,一个密闭的房子能让人更加安心,比如九年前的我。
他家在老别墅区,我小时候常来,因为我爸当时跟何家关系很好,我每年会来这里拜年,拜年的时候就会看见何许。
何许总是安分地站在何老爷子身边,对我们露出彬彬有礼的笑容。
不过后来他们搬家了。
程家出事后,何家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何老爷子嫌这个地段不吉利,就把房子给卖了。
辗转几次后,这房子落入了贺呈手中。
门是开着的,我敲敲门走进去,径直上了二楼。
二楼有一个巨大的圆厅,外圈围着整排的书架,上面很多书是贺呈搬进来后才放上去的,那些书曾陪伴我走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留声机里放着低沉的萨克斯独奏,古老的水晶灯无法将大厅完全照亮,暖黄的光温柔地洒下,为坐在地毯上看书的那个男人镀上一层柔和的滤镜。
他穿了一件黑色毛衣,像一只在白色毛绒地毯上打盹的黑猫。
贺呈听见我的脚步声,抬头冲我笑了笑。
他的眉眼很深邃,平时看人会显得有些深沉,唯有垂眼看书时会露出放松的神情,这会儿看我的眼神很平和,想来看的书应该挺合心意。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把冰糖雪梨递给他。
他舀了一勺:「昨天。」
「怎么不告诉我?」
「你忙。」他把碗底的糖水浇在雪梨上,「程大小姐身边那么多人,把时间花在我身上就浪费了。」
我懒得理会他话里的调侃,问他:「秦牧也和我公司的合作是不是你干的?」
他几口吃完了雪梨,拿纸巾擦了擦嘴,这才慢条斯理道:「稍稍推动了一下进度,本来也是属意于他的,再者我和秦家最近也有个合作,就当卖秦总一个小人情了。」
我无奈:「你没必要把他扯进来。」
他朝我伸出手,我和他对视,他温和地望着我,几秒后我只好将手放在他掌心。明明我站着他坐着,他却将主动权牢牢把控,这是他的习惯。
贺呈牵着我坐下,替我整理了一下头发:「给何许找点事做,他的注意力分散些比较好。」
我心道你都把他的身世透给何老爷子了难道还不够么?却也知道他决定的事无法更改,于是换了个话题:「你吃饭了么,我有点饿了。」
「想吃什么?厨师不在,我给你做。」
「炸酱面吧。」
第一次见面时贺呈为我做过一碗炸酱面。
九年前,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医院传来我父亲身死的消息。
他进 ICU 不过两天就撑不住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时间,等我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时,人已经在殡仪馆了。
程家各系亲戚吵成一团,公司里的股东也闹的不行,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我刚刚失去了父亲,有对我冷嘲热讽的,也有对我极尽巴结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想趁乱分一杯羹。
我对公司的事其实不甚了解,但何家在程家是占了股份的,很多人就把主意打到了何家身上,何许那时已经开始管事了,他是我爸钦定的女婿,很长一段时间都和我绑定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以为何家会对程家施以援手。
可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对当时的何家来说,帮助程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公司董事给何许打过电话,第三次才有人接。
电话那头他问:「出了这么大的事,程鹿清为什么不来见我?」
我爸生死未卜,公司乱成一团,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见他。
他在等我去见他,但他不会自己提出来。
何许总是喜欢这些弯弯绕绕,程家有意与何家联姻,所以他每年都送我许多礼物,在我生日那天空出时间来见我,有礼,规矩,一举一动都符合我爸的期许,至于我喜不喜欢他,那不在他考虑的范畴内。
我和秦牧也在一起的第一年,我本来想和他一起过生日,可我爸非说约了何许来家里做客,闹的我很不高兴,全程面无表情,气的我爸直瞪我。
何许就笑着和我爸说:「小鹿还小,没有在社会里磨砺过,有脾气很正常,玫瑰都是带刺的。」
那时他看我的眼神,宽容又冷漠。
我是一朵养在温室的玫瑰,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要被暴雨折弯了腰,便不得不屈服于他的保护。
他是这样想的。
那天何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可以来何家跟何许商量转移股权的事,最后提及何许的喜好:「来的时候带瓶豆奶吧,他爱喝这个。」
他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老了,不管事了,还是得看何许怎么想,提点我的样子像极了为我考虑的长辈。
可他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得意,得意我无依无靠,得意何许高高在上,得意曾经有意联姻的程何二家,现在要靠程家大小姐来讨好何家公子度过难关。
何老爷子希望我做一只乖乖听话的金丝雀,交出程家的一切,然后作为精致的展览品成列在何家的展柜里。
商人重利,一切皆可算计。这是何老爷子借程家磨难为何许上的一课。
但我没有去何家。
何许对我征服欲来自我十年如一日的冷淡,他有过许多女人,那些女人或求色或求财,唯有我,眼中从来没有他,也从不向他求什么。
他对我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
可他追求的人是不存在的,他想要女人高傲,又想要女人臣服,他天生带着征服欲,又将对他动心的女人弃之如履,这是死循环。
若我没有坚持,现在也不过是他的过客罢了。
我爸火化后,早就不耐烦的人们散去,留我一人坐在殡仪馆旁边的台阶上发呆。
我抱着他的骨灰盒,从正午坐到日渐西斜,天边燃起火烧云,下班的工作人员感叹:「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想的居然是,在作文里,这是对比的一种写法,用相反的天气来衬托主人公的内心情感。
我用语文老师的语气问自己,那么此刻主人公内心想的是什么呢?是她爸临死前交代的遗言:「和江柔葬一起」。
我被自己逗笑了,心说这他妈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去你妈的死老头,把我妈气死了还要跟你姘头合葬,你想都别想。
夕阳烧的我脸上一阵热意,泪水蒸发后脸因干燥而刺痛,我想站起来,可腿麻了,挣扎了半天干脆放弃抵抗,自暴自弃地等神经恢复。
这时有人挡住了光线,一片黑色风衣的衣摆垂在我眼前:「程鹿清。」
我抬头,逆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血红色的落日勾勒出他的轮廓,他有一个好看的下巴。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问了一句:「有烟么?」
他从口袋里拿出烟递给我,又挡着风替我点了火。
我叼着烟猛吸了一口,差点呛得咬不住。
他轻声笑了,衣摆一撩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慢慢来。」
我咳出了眼泪,不服输地又吸了一口,然后缓缓的吐出来,面前烟雾缭绕,忽然就觉得没那么难受了。
「挺好,有成为烟鬼的潜质。」他赞了一句。
我转头看他,这个男人有一张立体的脸,眉弓高,眼窝深,鼻子虽然挺但并不粗糙,显得有些俊秀,中和了立体眉眼的雕塑感。
他的下巴带点方,上面有零星胡茬,但并不影响他的整体气质,反而很有男人味。
看见他脸的瞬间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何许像他妈妈,长相偏阴柔,而何老爷子年轻时也算是一代青年才俊,据说他的大儿子,很像他。
男人见我看着他的脸不动,笑了笑自我介绍道:「我是贺呈。」
他是改了母姓的,他的母亲本就是个女强人,离了婚仍有生活和后盾,而我妈……嫁人以后完全丧失了自我,沉溺在过去无法自拔,不能接受我爸找小三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是自怨自艾,到最后含恨离去。
可笑的是我爸三个月后就把小三带回家了,那个江柔,看着柔柔弱弱,其实主意大的很,把我爸唬的神魂颠倒,往公司塞了一堆人,结果闹出了问题,让人卷钱跑了,我爸和她一起去追,要不是这样也不会出车祸。江柔当场死亡,我爸……过了几天也去陪她了。
我低头将情绪压住,冷着眼与贺呈对视,可能过了几分钟,也可能只是几秒,他忽然笑了。
他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包湿巾,抽出一张给我:「聊聊?」
我站起来,走下台阶:「送我去海边。」
他没问我做什么,开车带我往沿海公路去了,还很体贴地敞着篷,以便海风可以及时吹干我的眼泪。
我把骨灰都撒进了海里。
连同过去一起。
从那一刻起,程鹿清就是独身一人了。
「我饿了。」
我对贺呈说。
他带我回了临时住处,卷起袖子开始切葱:「炸酱面吃不吃?」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为了报复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择手段,却又有耐心陪我一个毫无根基的倒霉鬼浪费时间。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亲自下厨,他煮面时充满了烟火气,可解了围裙后办公的眼神又很锋利,察觉到我在看他,贺呈合上电脑为我倒了杯水,轻轻揉了揉我的发顶:「一切都有代价,你以后会懂。」
有了贺呈的帮忙,程家总算挺住了,虽然伤了点元气,但不至于被人吃干抹净。
「程鹿清,你太弱了。」贺呈替我稳住公司后说。
跟贺呈打交道其实很轻松,因为我们都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直来直往,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他对我很严厉,请了老师来辅导我功课,高考后更是直接带着我熟悉公司事务,手把手教我一切该学的。
他会用最平淡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问题,让我改文件改两个通宵,也会细心地察觉到我的体虚给我配中药调理,送我绝版的旧书。
他教我为人处事,教我长袖善舞,教我掩藏情绪,每次我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带我去海边看星星。
我们会脱了鞋光脚踩在沙滩上,感受海水的涨落,听风拂过海鸥翅膀的声音。
后来他将何家别墅买下来了,我往书架上添了不少书,我们就鲜少再出门看星星了。
自然的广袤星空洗涤人心,而浩瀚书海则给人沉静的力量。
公司事忙,偶有空闲时光,我们便会在圆厅里看书,我手边是咖啡,他手边是白水,手里拿本书,一天无言。
贺呈用五年时间,将我变成了一个和他很像的人。
我们用理智将自己牢牢锁住,情绪藏于内,精致且漠然。
然后我嫁给了何许。
带着程家做嫁妆,嫁给了何许。
何老爷子对我很满意。
贺呈也很满意。
后来他就很少再联系我了,他的生意做到了国外,只偶尔同我在电话里聊聊,谈及的也多是最近新看了一个画展或淘到一张老唱片。除非我问他,否则他轻易不会置喙我的公司管理。
去年他告诉我,他妈妈去世了。
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快见到他了。
贺呈将面端到我面前,手臂自然地搭在我背后的沙发上,我转头去看他。
岁月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有的只是时间的沉淀,他这样稳重又自持的男人,其实很讨小姑娘喜欢。
我在他身边的那几年,有数不尽的莺莺燕燕往他身上扑,他从不带女人回家过夜,但有一次一个相处了两个月的姑娘上门找了我,她问我拿什么迷魂汤蛊了贺呈,居然能住在他的房子里。
我给贺呈打电话,他甚至没有亲自到场,只派了两个保镖将那姑娘架走了。
那天晚上贺呈带回一张唱片,问我:「跳舞么?」
他对于跳舞这件事有很强的仪式感,特意换了西装。
我那时已经出席过很多酒会,他给我买了一整个衣柜的礼服,我挑了件黑色露背裙,行走间摇曳生姿。
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神暗了暗,随后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一手牵过我,一手轻扶我的腰肢。
那是一首安静的曲子,我们只小步地在圆厅中进退,我穿了高跟鞋,正好能将下巴放在他肩膀上。
我们沉默至一舞终了, 我抬起头看他,鼻尖只离他一指的距离,呼吸都能相互缠绕。
有人说,男女对视一分钟以上,很容易出事。
贺呈的眼眸像墨玉般温润却又时时透着悲悯,当他望着一个人时,对方很容易产生自惭形秽的想法,但我那时胆子很大,坚定不移地望着他,一定要等他的反应。
「程鹿清。」
他其实很少笑,但面对我时,却会习惯性牵起嘴角,连带着眼睛也染上笑意。
最后他打破了那一指的距离,抬起下巴,凉薄的唇在我额头上短暂停留了一秒。
若不是他的胡茬刺到了我,我几乎要以为那只是窗外漏进的风。
吃完面我去厨房把碗洗了,然后回到贺呈身边。
难得安宁。
我们就这样静坐,直到窗外响起一声鸟鸣,贺呈起身拉开窗帘,已至黄昏,透过落地窗倾斜进来,他从书架上取出一张黑胶唱片放在留声机上。
前奏响起,是 Careless Whisper。
转身向我伸出手,微微躬身:「跳舞么?」
我仍将下巴搭在贺呈肩膀上。
进退间他安抚地捏住我的后颈,「和从前一样。」
我握紧他的手以做回应。
一样么?不一样了。
我只是习惯了在他面前示弱,看他的眼神中永远带着依赖。
「你们合开的公司财政上有个大窟窿。」他说。
何家的动态一向是他最关心的。
我点头:「我知道。」
他笑:「他想要你折服,可我更喜欢你傲气。」
「他不会如愿。」
「你想好怎么处理了?」
我闭上眼,少年麋鹿般的眼睛一闪而过。
「很早之前,就想好了。」相关Tags:爱情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1914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