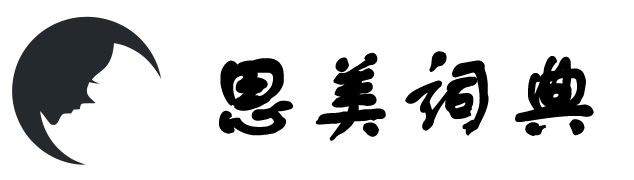邵柏港会相信谁?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还记得,那天明明是我和邵柏港的结婚纪念日。
我正准备下楼买菜烧大餐,兜里的手机却忽然震动。
我掏出一看,是一条短信和一张照片:
「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迟早都要吐出来」
照片上,邵柏港趴在病床边睡着了,而他的左手还紧紧握着谭盈雪纤细的手。
仿佛他一松开,她就会化掉。
抬脚——
可邵柏港昨晚给我的解释,明明是他在公司加班,好将今天空出来留给我们的纪念日。
踏空。
真的。
好痛啊。
后来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邵柏港赶到时也心疼极了,他为我忙前忙后,为照顾我累得眼下青黑。
可他的时间和精力明显被分割了。
一个心尖白月,一个红颜知己。
邵柏港将他的心分割,然后按照天平上的重要程度分配。
永远无法平等的分配。
就连同时养几只宠物的人都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何况是对会说会笑的人。
偏心但不越界,暧昧但不戳破。
邵柏港的天平摇摆,让本就被限制自由的我越发焦躁。
因而哪怕我尽力克制,我还是忍不住去作、去闹。
像是哭闹争宠的孩童,用更为激烈的方式去试探邵柏港对我爱的深浅,占有哪怕一丝的安全感。
可频繁的吃醋只会让感情变成累赘,越作越闹只会将爱人越推越远。
最后,在邵柏港一声「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失望叹息后,他渐渐以工作忙为借口,很少踏入我的病房。
看着谭盈雪每天发来炫耀的合照,我知道,她的计谋得逞了。
我坐在孤寂的病房里,盯着明亮的窗外发呆。
初恋,心存遗憾,很可能玉殒香消、天人永隔。
谭盈雪还真是摸透了男人心。
我不由得又想起儿时的幻想游戏。
假如,是我突然死了呢?
邵柏港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我真的很想知道。
于是我闭眼凝神,开始编造自己的死法。
而这次被我拖入幻境的对象。
是整个世界。
幻境,开始——
6
她死的那天,天晴朗极了。
街道两旁的香樟树生机勃勃,每片叶子都剔透得好似翡翠。
邵柏港在窗边点了一支烟,手却抖得厉害。
他的爱人,他的妻子。
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
邵柏港将一大口烟吞进肺部。
像是吸了一大口柏油热气,喉咙被刮得生疼。
明明那天早晨她还和他发了微信,说她要出院了,问他能不能来接她回家。
当时他怎么回复的来着?
他回在公司忙,会派司机去接她。
然后他就将手机静音,继续坐在医院的花园长椅上,与谭盈雪追忆往事。
比如某个高中同学现在在哪儿工作,大学时谁犯的某件蠢事至今半夜想起还会尴尬。
那一整天的阳光都很好,他们也追忆得很开心。
当他傍晚推门回家时,先有欢快的轻音乐灌入双耳,后有凉掉的菜香充斥鼻腔。
而他的她系着围裙坐在阳台,披着橘粉色的晚霞,安静极了。
黑屏的手机摆在茶几上,宛如一只优雅的黑猫,守着一旁白色的药瓶。
以及撒了一地的安眠药。
他梦游似的走进,手机密码还是他的生日。
里面最新收到的短信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他和谭盈雪坐在阳光明媚的花园,相望笑得默契又轻快……
烟尾燃起的火光忽然刺痛了邵柏港的眼睛,烟灰掉落在鞋尖。
烧灼感隔着皮鞋烫伤脚背,邵柏港恍惚地低头去看,手抖得再也夹不住香烟。
他几乎能想象到那天发生的一切——
她被司机接送回家,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决定转换心情。
于是她打开小音箱,哼着歌准备大烧一餐,晚上与他一起庆祝她的出院。
她在厨房哼着歌,锅铲随着节奏挥舞,陡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她看见短信附着的照片,先是一怔,手里的锅铲还能顺着惯性翻炒几下。
接着在某一瞬间,整个人死死凝固。
那一刻的她,会想什么?
是她才烧好的这一桌热腾腾佳肴配上红酒会有多美味?
还是那又干又涩的安眠药要一颗一颗吞下去多少才会最快起效?
邵柏港不敢再去细想,只觉得他的心脏疼得快要裂开。
那天在他将手机静音后,她发给他的最后两条微信是:
「等你忙完回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吧,关于谭盈雪,关于这些天,关于我们的未来」
「我很爱你,很珍惜你,我不想失去你」
爱、珍惜、失去……
她。
邵柏港右手攥住上心口,像是无法呼吸,闷哼出一阵困兽似的呻吟。
她,死了。
永远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再也再也,找不回来了。
也就在这时,一串喧哗爆发在医院的长廊,由远及近快到像是劈来的天雷。
邵柏港迟钝地回头,一个拳头就以十分力砸在他的脸上。
「砰!」
邵柏港整个人直接飞出去,脑袋撞上窗台发出可怕的重响。
「邵柏港!我他妈杀了你!」
冲进病房的顾卓双目被血丝织成血红,脖颈上青筋暴起。
他一把拽起瞳孔涣散的邵柏港,疯了似的一拳接一拳,血很快糊了满手。
「啊!」
追上来的谭盈雪还推着点滴架,她惊恐尖叫一声,想过来阻拦,又被杀红眼的顾卓吓得不敢靠近。
「卓哥!」
而第二个追进病房的是楚坤。
「卓哥你冷静点!」
可楚坤根本拉不开顾卓,反倒被失去理智的顾卓误伤。
「顾卓你他妈给我冷静点!!」
楚坤踉跄着蹭去脸上的鼻血,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现在要是进去了!谁来带阿寅回家?!」
带阿寅回家。
这句话就像是个魔咒,一下将发狂的顾卓定在原地。
楚坤趁机将顾卓一把摔开,自己却就近抄起病房里的一把椅子。
他扭头冲谭盈雪一笑,连虎牙上都沾上了血:「看好了,下一个就是你。」
然后在谭盈雪和顾卓的呆滞中,楚坤将椅子高高举起——
「楚坤!」
我徒劳地伸手大喊。
可在这幻境中,我就像个隐形人,谁也看不见我。
「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下!三下!五下!
直到安保冲进病房将楚坤强行制服,楚坤手中的椅子才停止可怖的变形。
邵柏港蜷缩在地,哀嚎得不似人声。
他的两条小腿悬在膝盖下,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
周围吵得好似炸开的鞭炮,可我却清楚听见鲜血滴落的噼啪声。
以及我心脏狂跳的警报声。
太过了……
太过了、太过了!
我只是想看邵柏港懊悔。
只是想看他在我死后如何忏悔、如何悲恸、如何幡然醒悟、如何后悔不好好珍惜眼前人。
我从没想看顾卓癫狂,看楚坤为替我报仇而被警察带走。
不行,我要解除幻境,我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解除、解除!
解除啊!
我站在忙乱的人群中拼命大喊。
可直到我喊哑了嗓子,也没有一人注意到真正的我的存在。
完了。
我呆滞在人群中央,脸上的泪逐渐变得冰凉。
超能力失控了。
幻境,解除不了了。
7
在没有被邀请的前提下,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来送「我」的人不少,那天来参加我和邵柏港订婚宴的人,换上黑色的衣服和悲伤的表情后再次与我重逢。
除了邵柏港和楚坤。
邵柏港在医院抢救,谭盈雪陪他,楚坤也面临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只有顾卓一人主持着葬礼。
或者说,是只有他一人在搅乱葬礼。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顾卓哭。
从小到大顾卓都倔得要死,一身皮肉像是铁打的,被爷爷吊房梁上拿皮带抽都能一声不吭,
反倒是我被吓得哇哇大哭,顾卓被放下来后就拿从爷爷那儿偷来的钱买糖吃。
他一颗,我一颗,他一颗,我一颗……
后来顾卓分得烦了,干脆把糖全丢给我,美其名曰「小孩子才爱吃糖」。
我含着两泡泪吃得美滋滋,楚坤则在一旁看得一脸鄙夷。
而顾卓唯一一次差点哭了,还是在我高三。
那年我和邻班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但纯粹只是友谊,却被班上不怀好意的人举报给班主任。
高考临近,我受压力影响成绩有所下滑,班主任便将原因笼统归结于「早恋」二字,请顾卓到学校谈话。
正巧那天我和那男生在走廊碰见,刚彼此笑着打声招呼。
暴怒如狮子的顾卓就冲了过来,一把推开要和我勾肩搭背的男生。
我惊讶于顾卓的到来,又见朋友被他推倒,气又急地喊了声「哥你干嘛?!」
然后「啪!」的一个巴掌就将我的脸打偏。
当着全班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的面,甚至当着其他班我不认识的同学的面。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顾卓。
顾卓自己也愣住,他眼眶红了,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
而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一字一字清楚又愤恨地对他说:
「我不会原谅你。」
「我恨你。」
此刻,望着抱着我的棺材失声痛哭的顾卓,我眼泪断线似的掉,忽地又「噗嗤」一声笑了。
顾卓他哭得真的好难听。
像是被活活打死的人发出的绝望嚎叫,难怪他从来不哭。
几个人过来想将顾卓从我的棺材上拉开,顾卓大哭挣扎着,膝盖重重磕在地上。
我看着他,心里有那么一丝丝替高三的自己解恨的快意。
但紧随其后的,只有铺天盖地的委屈与悲伤。
『顾卓……』
我试图走近他,伸出徒劳的手想触碰顾卓,哭得难看极了:『顾卓我没死,顾卓我在这,我就在这……』
却见顾卓冷不丁一僵,他不再挣扎,一动不动像是在一片抽泣里分辨谁的声音。
「我听见了!」
顾卓忽然大喊起来:「我听见顾寅的声音了!她没死!她还活着!」
我一呆。
顾卓红着眼扑向棺材,疯了似的想打开:「我妹妹还活着!我妹妹才不可能自杀!她小时候最爱吃糖了,她那么怕苦,怎么可能吃得下半瓶安眠药!」
这时候掀棺材是大忌,其余被吓呆的人忙回神上前拉扯他。
「滚开!滚开!我妹妹还活着!她在等着我救她!我要救她!我要救她!」
顾卓在众人手里拼命挣扎,扒住的十指在棺材的木板上抠出血来:
「哥哥错了,阿寅哥哥错了!你不是说梦想是周游世界吗?哥哥现在就陪你去,你想去哪就去哪!阿寅你回来吧,求求你回来吧!」
『哥……哥!』
我瘫坐在地。
嚎啕大哭。
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去赌他人的真心。
真是愚蠢透了。
邵柏港会相信谁?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还记得,那天明明是我和邵柏港的结婚纪念日。
我正准备下楼买菜烧大餐,兜里的手机却忽然震动。
我掏出一看,是一条短信和一张照片:
「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迟早都要吐出来」
照片上,邵柏港趴在病床边睡着了,而他的左手还紧紧握着谭盈雪纤细的手。
仿佛他一松开,她就会化掉。
抬脚——
可邵柏港昨晚给我的解释,明明是他在公司加班,好将今天空出来留给我们的纪念日。
踏空。
真的。
好痛啊。
后来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邵柏港赶到时也心疼极了,他为我忙前忙后,为照顾我累得眼下青黑。
可他的时间和精力明显被分割了。
一个心尖白月,一个红颜知己。
邵柏港将他的心分割,然后按照天平上的重要程度分配。
永远无法平等的分配。
就连同时养几只宠物的人都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何况是对会说会笑的人。
偏心但不越界,暧昧但不戳破。
邵柏港的天平摇摆,让本就被限制自由的我越发焦躁。
因而哪怕我尽力克制,我还是忍不住去作、去闹。
像是哭闹争宠的孩童,用更为激烈的方式去试探邵柏港对我爱的深浅,占有哪怕一丝的安全感。
可频繁的吃醋只会让感情变成累赘,越作越闹只会将爱人越推越远。
最后,在邵柏港一声「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失望叹息后,他渐渐以工作忙为借口,很少踏入我的病房。
看着谭盈雪每天发来炫耀的合照,我知道,她的计谋得逞了。
我坐在孤寂的病房里,盯着明亮的窗外发呆。
初恋,心存遗憾,很可能玉殒香消、天人永隔。
谭盈雪还真是摸透了男人心。
我不由得又想起儿时的幻想游戏。
假如,是我突然死了呢?
邵柏港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我真的很想知道。
于是我闭眼凝神,开始编造自己的死法。
而这次被我拖入幻境的对象。
是整个世界。
幻境,开始——
6
她死的那天,天晴朗极了。
街道两旁的香樟树生机勃勃,每片叶子都剔透得好似翡翠。
邵柏港在窗边点了一支烟,手却抖得厉害。
他的爱人,他的妻子。
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
邵柏港将一大口烟吞进肺部。
像是吸了一大口柏油热气,喉咙被刮得生疼。
明明那天早晨她还和他发了微信,说她要出院了,问他能不能来接她回家。
当时他怎么回复的来着?
他回在公司忙,会派司机去接她。
然后他就将手机静音,继续坐在医院的花园长椅上,与谭盈雪追忆往事。
比如某个高中同学现在在哪儿工作,大学时谁犯的某件蠢事至今半夜想起还会尴尬。
那一整天的阳光都很好,他们也追忆得很开心。
当他傍晚推门回家时,先有欢快的轻音乐灌入双耳,后有凉掉的菜香充斥鼻腔。
而他的她系着围裙坐在阳台,披着橘粉色的晚霞,安静极了。
黑屏的手机摆在茶几上,宛如一只优雅的黑猫,守着一旁白色的药瓶。
以及撒了一地的安眠药。
他梦游似的走进,手机密码还是他的生日。
里面最新收到的短信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他和谭盈雪坐在阳光明媚的花园,相望笑得默契又轻快……
烟尾燃起的火光忽然刺痛了邵柏港的眼睛,烟灰掉落在鞋尖。
烧灼感隔着皮鞋烫伤脚背,邵柏港恍惚地低头去看,手抖得再也夹不住香烟。
他几乎能想象到那天发生的一切——
她被司机接送回家,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决定转换心情。
于是她打开小音箱,哼着歌准备大烧一餐,晚上与他一起庆祝她的出院。
她在厨房哼着歌,锅铲随着节奏挥舞,陡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她看见短信附着的照片,先是一怔,手里的锅铲还能顺着惯性翻炒几下。
接着在某一瞬间,整个人死死凝固。
那一刻的她,会想什么?
是她才烧好的这一桌热腾腾佳肴配上红酒会有多美味?
还是那又干又涩的安眠药要一颗一颗吞下去多少才会最快起效?
邵柏港不敢再去细想,只觉得他的心脏疼得快要裂开。
那天在他将手机静音后,她发给他的最后两条微信是:
「等你忙完回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吧,关于谭盈雪,关于这些天,关于我们的未来」
「我很爱你,很珍惜你,我不想失去你」
爱、珍惜、失去……
她。
邵柏港右手攥住上心口,像是无法呼吸,闷哼出一阵困兽似的呻吟。
她,死了。
永远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再也再也,找不回来了。
也就在这时,一串喧哗爆发在医院的长廊,由远及近快到像是劈来的天雷。
邵柏港迟钝地回头,一个拳头就以十分力砸在他的脸上。
「砰!」
邵柏港整个人直接飞出去,脑袋撞上窗台发出可怕的重响。
「邵柏港!我他妈杀了你!」
冲进病房的顾卓双目被血丝织成血红,脖颈上青筋暴起。
他一把拽起瞳孔涣散的邵柏港,疯了似的一拳接一拳,血很快糊了满手。
「啊!」
追上来的谭盈雪还推着点滴架,她惊恐尖叫一声,想过来阻拦,又被杀红眼的顾卓吓得不敢靠近。
「卓哥!」
而第二个追进病房的是楚坤。
「卓哥你冷静点!」
可楚坤根本拉不开顾卓,反倒被失去理智的顾卓误伤。
「顾卓你他妈给我冷静点!!」
楚坤踉跄着蹭去脸上的鼻血,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现在要是进去了!谁来带阿寅回家?!」
带阿寅回家。
这句话就像是个魔咒,一下将发狂的顾卓定在原地。
楚坤趁机将顾卓一把摔开,自己却就近抄起病房里的一把椅子。
他扭头冲谭盈雪一笑,连虎牙上都沾上了血:「看好了,下一个就是你。」
然后在谭盈雪和顾卓的呆滞中,楚坤将椅子高高举起——
「楚坤!」
我徒劳地伸手大喊。
可在这幻境中,我就像个隐形人,谁也看不见我。
「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下!三下!五下!
直到安保冲进病房将楚坤强行制服,楚坤手中的椅子才停止可怖的变形。
邵柏港蜷缩在地,哀嚎得不似人声。
他的两条小腿悬在膝盖下,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
周围吵得好似炸开的鞭炮,可我却清楚听见鲜血滴落的噼啪声。
以及我心脏狂跳的警报声。
太过了……
太过了、太过了!
我只是想看邵柏港懊悔。
只是想看他在我死后如何忏悔、如何悲恸、如何幡然醒悟、如何后悔不好好珍惜眼前人。
我从没想看顾卓癫狂,看楚坤为替我报仇而被警察带走。
不行,我要解除幻境,我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解除、解除!
解除啊!
我站在忙乱的人群中拼命大喊。
可直到我喊哑了嗓子,也没有一人注意到真正的我的存在。
完了。
我呆滞在人群中央,脸上的泪逐渐变得冰凉。
超能力失控了。
幻境,解除不了了。
7
在没有被邀请的前提下,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来送「我」的人不少,那天来参加我和邵柏港订婚宴的人,换上黑色的衣服和悲伤的表情后再次与我重逢。
除了邵柏港和楚坤。
邵柏港在医院抢救,谭盈雪陪他,楚坤也面临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只有顾卓一人主持着葬礼。
或者说,是只有他一人在搅乱葬礼。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顾卓哭。
从小到大顾卓都倔得要死,一身皮肉像是铁打的,被爷爷吊房梁上拿皮带抽都能一声不吭,
反倒是我被吓得哇哇大哭,顾卓被放下来后就拿从爷爷那儿偷来的钱买糖吃。
他一颗,我一颗,他一颗,我一颗……
后来顾卓分得烦了,干脆把糖全丢给我,美其名曰「小孩子才爱吃糖」。
我含着两泡泪吃得美滋滋,楚坤则在一旁看得一脸鄙夷。
而顾卓唯一一次差点哭了,还是在我高三。
那年我和邻班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但纯粹只是友谊,却被班上不怀好意的人举报给班主任。
高考临近,我受压力影响成绩有所下滑,班主任便将原因笼统归结于「早恋」二字,请顾卓到学校谈话。
正巧那天我和那男生在走廊碰见,刚彼此笑着打声招呼。
暴怒如狮子的顾卓就冲了过来,一把推开要和我勾肩搭背的男生。
我惊讶于顾卓的到来,又见朋友被他推倒,气又急地喊了声「哥你干嘛?!」
然后「啪!」的一个巴掌就将我的脸打偏。
当着全班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的面,甚至当着其他班我不认识的同学的面。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顾卓。
顾卓自己也愣住,他眼眶红了,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
而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一字一字清楚又愤恨地对他说:
「我不会原谅你。」
「我恨你。」
此刻,望着抱着我的棺材失声痛哭的顾卓,我眼泪断线似的掉,忽地又「噗嗤」一声笑了。
顾卓他哭得真的好难听。
像是被活活打死的人发出的绝望嚎叫,难怪他从来不哭。
几个人过来想将顾卓从我的棺材上拉开,顾卓大哭挣扎着,膝盖重重磕在地上。
我看着他,心里有那么一丝丝替高三的自己解恨的快意。
但紧随其后的,只有铺天盖地的委屈与悲伤。
『顾卓……』
我试图走近他,伸出徒劳的手想触碰顾卓,哭得难看极了:『顾卓我没死,顾卓我在这,我就在这……』
却见顾卓冷不丁一僵,他不再挣扎,一动不动像是在一片抽泣里分辨谁的声音。
「我听见了!」
顾卓忽然大喊起来:「我听见顾寅的声音了!她没死!她还活着!」
我一呆。
顾卓红着眼扑向棺材,疯了似的想打开:「我妹妹还活着!我妹妹才不可能自杀!她小时候最爱吃糖了,她那么怕苦,怎么可能吃得下半瓶安眠药!」
这时候掀棺材是大忌,其余被吓呆的人忙回神上前拉扯他。
「滚开!滚开!我妹妹还活着!她在等着我救她!我要救她!我要救她!」
顾卓在众人手里拼命挣扎,扒住的十指在棺材的木板上抠出血来:
「哥哥错了,阿寅哥哥错了!你不是说梦想是周游世界吗?哥哥现在就陪你去,你想去哪就去哪!阿寅你回来吧,求求你回来吧!」
『哥……哥!』
我瘫坐在地。
嚎啕大哭。
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去赌他人的真心。
真是愚蠢透了。
相关Tags:分手生命喜欢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1873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