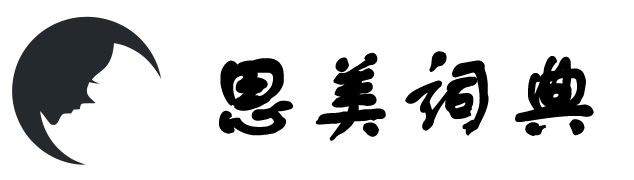上一世,他这样说过之后,我便再也没敢矫情。
我闭紧了嘴,披紧了他的披风,乖乖缩进他怀里。
他拽紧了缰绳也抱紧了我,我被他的温暖包裹着,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马蹄声,心跳声很乱,身体却不再冷了。
这一世,他又问我,嫌不嫌他脏。
我把唇贴向他的耳廓,一字一句:
「秦宴,你不脏,你比谁都干净。
「脏的是你爹,他脏了你娘的身子,还脏了你的人生。
「脏的是那些拜高踩低的蠢货,他们的脑子早就被灌满了溲水,他们的污嘴,根本不配提你的名字。
「秦宴,这座秦府配不上你,早点离开可好?」
一阵落针可闻的寂静之后……
秦宴忽然把头埋向我的颈窝,呼吸温热,似撩拨又似戏谑:
「呵,苏妙小姐把我夸得这样好,我又该为苏妙小姐做些什么才好?」
「简单啊~」
我笑:
「我欲杀人时,你来做我的刀。
「我欲救人时,你来做我的药。
「我欲嫁人时,你来做我的郎。」
秦宴直勾勾地盯着我,瞳孔微震,凤眸极深:
「你的刀,你的药,你的……郎?」
9
秦宴就算装得再清冷沉默,骨子的病态也还是藏不住。
那双眼睛里,分明汹涌着痴妄的情思。
我索性去推阁楼的门:
「秦宴,别装了。你不是早就盯上我了吗?这里面,满屋子挂的全都是我的画像,我说得对不对?」
嘎吱一声,门开了。
我却傻眼了——
画呢?
一幅我的画像都没有?!
夕阳余晖,透过窗棂,书卷整整齐齐,列满柜阁。
「诶……这一年,是还没画吗?」
我没忍住,叨咕了一句,略微尴尬地回头,朝秦宴望去。
只见,苍白阴郁的少年眉梢微挑,薄唇勾笑:
「原来苏妙小姐是想让我为你作画,还想要挂满这间屋子?」
「……」
误会大了。
秦宴从高阁上取下《川域志》一书,递到我的手中。
我接过之后,便转身欲走。
秦宴却忽然拉住我,捧起我的脸,眼尾泛红,目光是病态的偏执,声音里带着撩人的蛊惑:
「妙妙姑娘是怎么猜到我心思的?
「我把妙妙画满这间屋子,妙妙就是我的了……可好?
「明日就开始画,行不行?
「妙妙、妙妙……」
10
年少的疯子,也还是疯子。
秦宴说着狂悖不堪的情话,唇齿间不断呢喃着我的名字。
声音渐哑,语气渐轻。
我扬起脸,看到少年漆黑的眸里正翻涌着深渊般的欲念。
「秦宴,你从前真是好会装。」
我将唇贴在他的侧脸上,轻吻浅啄,又迅速离开。
秦宴错愕了一瞬。
很快,他眼尾的红晕便越来越浓。
再开口时,他嗓子已经哑得不像话:
「妙妙姑娘是小狸奴投生的吧?
「将人心勾缠走了,却又不负责了?」
他问得无奈又委屈,卑微又放肆,迷乱又克制。
我但笑不语,只戏谑地望着他。
我一直不知道秦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盯上的我。
他此刻,是已经把我当成他的私有物了么?
那样说来,他盯上我,便该是在更早以前……
11
我仔细回想。
在我及笄之前的年岁里,与秦宴的交集大约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一个冬日。
那年,下了一场瑞雪。
我带着侍女出门赏雪,本想寻个僻静之地,却误打误撞,看到了秦宴。
他正被几个世族公子按在雪地里打骂。
我又惊又怒地扬声喝止。
那几人认出我的身份,碍于太傅府的面子,终于肯收手散去。
秦宴目光阴冷,始终绷着神色,固执地不肯示弱。
直到那些人走远之后,他才终于绷不住,咳了几口血。
血色殷红,落在皑皑白雪上,触目惊心。
我下意识扶了他一下,掏出帕子给他用,又吩咐侍女阿春去寻人帮忙。
可秦宴只踉跄了一瞬,便强撑着站回风雪里:
「不必。」
他垂眸盯向我手里那方沾染了他的血迹的丝帕,薄唇间溢出一丝自嘲的凉笑:
「苏小姐还是离我这种人远些,免得脏了自己。」
他说完便走,颀长单薄的背影与雪色融为一体。
那是我第一次记住他的样子。
倔强,阴郁,狠绝,孤独。
像是蛰伏的兽。
12
我与许多世家公子贵女们一同长大。
世家交往大多以利为先。
人们看不起秦宴,自然更不会去亲近他——这个贱妓所出,毫无希望的秦家庶子。
我却头衔颇多:
太傅府嫡长女、京城第一才女、未来的太子妃。
所以……
我一向是被众星拱月的那个。
而秦宴,一向是被孤立的那个。
京中世族就这么几家,年年盛事欢宴,总有碰面的时候。
自那次之后,我又远远地见过秦宴几次。
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淡淡看着远处的喧嚣,眼底偶然间会闪过一丝不屑。
我与他也有过眼神对上的刹那。
我会对他莞尔示意。
他则冷冷淡淡地错开目光。
有人在背地里讽他——
说他那张脸长得勾魂摄魄,像极了他那个花魁娘亲,一瞧就是下贱胚子。
我听着不爽。
这种时候,我那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便能派上用场。
我会端着最文静贤淑的样子,笑不露齿,礼貌地提醒那些人:
「闲谈论人非,实非君子淑女所为,慎言慎言。
「与其背后说人短,不如静坐思己过。」
……
有时,我厌烦得很了,也会勾着笑,懒洋洋地给那些人讲:
「听说啊,地府分十八层。
「第一层,便是拔舌地狱。
「凡是挑拨离间、多嘴多舌、诽谤加害、说谎骗人者,死后都会被打入这一层。小鬼会掰开那人的嘴,铁钳夹舌,生生拔下……但是又非一下拔下,而是拉长,慢拽……」
讲完,我面不改色,佯作淡然地摇扇饮茶。
天知道,我有多么厌恶他们的聒噪。
天知道,我每天装温良淑女有多累。
天知道,我烦得想拔了他们的舌头。
这招总是比温言温语的提醒更奏效。
每每我这样说,周围便会立时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只不过……
再奏效的手段,也偶尔会有意外。
那一次,旁人听了我的拔舌地狱之谈,皆收敛闭嘴。
可偏偏——
我背后却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呵笑。
我小心翼翼地回头……
居然瞧见了秦宴。
他不知何时来的,正站在我身后,一双深眸凝着我,似笑非笑。
世上最尴尬之事莫过于此。
我那时生怕他误会,急忙解释:
「秦少公子,我并非在背后议论你,我只是……」
可秦宴根本不待我说完,便薄唇开合,唤我名字:
「苏妙姑娘。」
我有些茫然:
「嗯?」
他问:
「若拔舌地狱是第一层,那后面的十七层呢,又是怎样的地狱?」
我答:
「第二层是剪刀地狱、第三层铁树地狱、第四层孽镜地狱……」
说着说着,我便意识到不对,赶紧停了下来。
我顶着京城才女的名头,读的应该都是贤者文章,诸子百家。
地狱之说,是我从杂谈野志上瞧来的。
偶然一句无妨,可要是再往下数,内容实在过于阴间,便与我的身份很不相宜了。
我有些气,偷偷瞪他。
亏我之前还暗中维护他,他竟想坑我?
秦宴却勾了勾唇角:
「若有朝一日,能听苏妙姑娘将后面十八层的故事都讲完就好了。」
……
这便是我及笄之前,与秦宴的两次交集。
第一次,我撞见他雪中的狼狈。
第二次,他看透我人前的伪装。
所以,这个狼崽子,居然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了?
13
从记忆中回过神来,窗外日头已经西斜。
我从秦宴的怀中离开,手中捏着他给我的那本《川域志》,随手翻了翻,倚门而笑:
「秦宴,想知道第五层地狱是什么吗?」
他垂眸盯着我,一开口,尾音上撩:
「怎么,妙妙姑娘终于愿意讲了?」
我却道:
「下个月的秋猎围场,你我联手,若能赢了容玉太子,我便讲给你听。」
……
这年的秋猎,会有一场刺杀。
容玉太子在这一局里救驾有功,经此一事,此后更是深得圣宠。
可其实,容玉早就获悉了敌国那些刺客们的计划。
他故意隐瞒不报,就是为了博得救驾之功。
而我那庶妹苏明颜,更是心思歹绝,她避险途中,居然趁乱把我推到了刺客的刀下,意图要了我的命。
是秦宴替我挨了一刀,又反手把那刺客杀了。
可那刀上有毒……
我至今记得他衣袍染血的模样。
上辈子,拜这一刀所赐,秦宴落下了病根。
以至于后来,他即便位极人臣,寻尽天下珍药,也终究寿数难续。
这一世——
我要让苏明颜和容玉太子一起,来偿还这一刀的债!
只不过……
我却忘了,秦宴这疯子,向来是个贪心的。
他凑近我,扬唇一笑:
「妙妙,不够的。
「我若赢了他,你得在洞房之夜的喜床上讲给我听,才行……」
14
秦宴厮磨的气音在我耳边掀起热浪。
我笑着答应他:
「好,听你的。」
抱着书册扶梯而下时,我听到秦宴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忽然有些相信妙妙姑娘先前的那些梦话了。
「妙妙姑娘忽然转了性,待我这般好,是因为在那场梦魇里,有所遗憾吗?」
我回眸望他,诸多心酸,化作一句:
「是啊,梦里遗憾颇多。」
只见秦宴懒洋洋斜靠着门,笑弧惑人:
「看来,那确实不是什么好梦。
「不过,我曾梦过妙妙上千遍,妙妙这才只梦了我一遍。
「依我看,妙妙不如摒弃忧思,乖乖吃饭,好好睡觉,再多梦我几次。
「说不定下一次,便是好梦了。」
我鼻子一酸,不禁点头称是。
我知他一直望着我,可我却不敢再去看他灼热的眼神,匆忙应过,便赶紧走了。
我生怕再待下去,会在他面前哭红了眼。
15
上一世,他也说过不少情话。
只是我从来都不大相信,自然也鲜少回应他。
我见过他杀人时血溅满身的样子。
也见过他面无表情地将人四肢斩下,泡到酒缸中施以极刑的残忍手段。
所以,他的情话,在那时的我听来,更像疯话。
尤其是当我得知他爬上高位的手段之后——
秦宴少时受尽欺辱凌虐,伤病诸多。
为了韬光养晦,他故意隐忍不发。
但他其实从小就偷偷地习文、练剑、拉拢人才。
他在暗中,伪装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专门与京城权贵们做生意敛财。
看似卑贱如泥的少年。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堆金砌玉。
一切,只差一个青云直上的机会。
机会随时可以谋。
可他的余生,却被我毁了。
秋日围猎的那场刺杀,他救我或许只是顺手。
谁知那刀不惹眼,那毒却致命,短短几年,便送他去见了阎王。
他委实是赔大发了。
起初几年,他尚可以靠药物维持,装作身无大碍的样子,在朝中肆意翻弄权柄。
没人看出他的破绽。
而我,是在太傅府落败,被罚没入贱籍的那一年,才被秦宴带走的。
当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那其实已经是秦宴生命的最后一年。
我被他囚在深苑里,听到了从他房中传来压抑不住的咳嗽,闻到了他院子里经久不散的药气,又看到他呕血之后来不及换下的脏衣,才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倒也无意瞒我,甚至还学会了挟病图报:
「我都快死了,妙妙还不肯说两句好听的哄哄我?
「真是无情,你就那么喜欢太子?哼,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人说,冲喜能续命,要不……妙妙给我冲喜试试?
「不答应就算了,别用那刀子似的眼神瞪我。
「我这府邸是能吃人吗?你就那么急着离开?
「等我死了,再放你走行不行?」
其实我与太子,顶多算是青梅竹马之谊,谈不上喜欢或爱。
更何况,当我得知是太子害死我弟弟的那一刻起,对他就只剩下恨了。
秦宴却闲来无事总会酸上太子几句,一边酸还一边观察我的神色。
我不信秦宴是真的看上了我,我猜他大概是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多年的筹谋,全毁在了救我的那一刻。
所以他才囚我于深苑,要我陪着他,伺候他,以满足他那偏执的私欲。
最无语凝噎的是……
我从小养在深闺,在太傅府落败之前,连一丁点的重物都没提过。
他却非要教我练剑。
那剑沉得要死,我拿一会儿就手酸,赌气扔在地上不肯练。
秦宴难得在我面前阴了脸:
「匕首你嫌短,刀剑你嫌沉。
「暗器你嫌丢不准,射箭你又嫌胳膊疼。
「妙妙的手真是矜贵,到底教什么,你才肯学?」
我反唇相讥:
「我学那些做什么?像你一样,动不动就杀人吗?」
他笑了,大约是气笑的。
因为他笑过两声之后,脸色便骤然苍白,蹙眉重咳,竟呕出一口血来。
我以为他终会放弃的。
可他缓过来之后,却又淡然地拭净唇边血线,让我继续,还笑吟吟地威胁我:
「妙妙今日若是还学不会摘叶飞花,便伺候我沐浴吧,可好?」
我心里骂他是疯子。
可他这话却总有奇效。
为了不去伺候他沐浴更衣,承欢身下,我到底学会了不少东西。
只是渐渐地,我眼看着秦宴从一个风华绝艳的公子,变成了垂死挣扎的困兽。
他的手越发无力。
他握不稳剑了,也拿不动弓了。
终于轮到我笑话他:
「你为奸作恶,即使身居高位,活着又有何趣?待你死后,世上没人为你哭,他们只会欢呼。」
秦宴盯着我,反问:
「你也不会哭?」
我连想都不想:
「不会。」
他失神了一下,才缓缓嗤笑:
「嗯,那活着确实无趣。」
我便又道:
「那你为何还活?
「不如断了药石,死了干脆。」
他被我咒了也不怒,只是阴郁的脸上满是无奈:
「没良心的小狸奴,我若死了谁来护你?
「教了你半天,你却连只鸡都不肯杀。
「我若不把那些想害你的人都杀尽,又怎么敢死?」
一般时候,他喜欢叫我妙妙。
他说这名字像在唤猫。
所以,当他偶尔不怎么高兴时,便喊我小狸奴。
等到秦宴终于肯放我离开的那日,他已是病容枯槁。
他连说话都费极了力气,眼神却偏偏还带着狠意:
「我死后,你便不许再怨我、厌我了。
「否则我便化身厉鬼,夜夜逢你春梦,与你欢愉纠缠,扰你不得安……」
说到一半,他又忽然顿住。
终究苦笑一声,无奈地红了眼:
「罢了。
「你放心吧,这个世上不会有鬼。
「也不会再有我了。」
上一世,他这样说过之后,我便再也没敢矫情。
我闭紧了嘴,披紧了他的披风,乖乖缩进他怀里。
他拽紧了缰绳也抱紧了我,我被他的温暖包裹着,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马蹄声,心跳声很乱,身体却不再冷了。
这一世,他又问我,嫌不嫌他脏。
我把唇贴向他的耳廓,一字一句:
「秦宴,你不脏,你比谁都干净。
「脏的是你爹,他脏了你娘的身子,还脏了你的人生。
「脏的是那些拜高踩低的蠢货,他们的脑子早就被灌满了溲水,他们的污嘴,根本不配提你的名字。
「秦宴,这座秦府配不上你,早点离开可好?」
一阵落针可闻的寂静之后……
秦宴忽然把头埋向我的颈窝,呼吸温热,似撩拨又似戏谑:
「呵,苏妙小姐把我夸得这样好,我又该为苏妙小姐做些什么才好?」
「简单啊~」
我笑:
「我欲杀人时,你来做我的刀。
「我欲救人时,你来做我的药。
「我欲嫁人时,你来做我的郎。」
秦宴直勾勾地盯着我,瞳孔微震,凤眸极深:
「你的刀,你的药,你的……郎?」
9
秦宴就算装得再清冷沉默,骨子的病态也还是藏不住。
那双眼睛里,分明汹涌着痴妄的情思。
我索性去推阁楼的门:
「秦宴,别装了。你不是早就盯上我了吗?这里面,满屋子挂的全都是我的画像,我说得对不对?」
嘎吱一声,门开了。
我却傻眼了——
画呢?
一幅我的画像都没有?!
夕阳余晖,透过窗棂,书卷整整齐齐,列满柜阁。
「诶……这一年,是还没画吗?」
我没忍住,叨咕了一句,略微尴尬地回头,朝秦宴望去。
只见,苍白阴郁的少年眉梢微挑,薄唇勾笑:
「原来苏妙小姐是想让我为你作画,还想要挂满这间屋子?」
「……」
误会大了。
秦宴从高阁上取下《川域志》一书,递到我的手中。
我接过之后,便转身欲走。
秦宴却忽然拉住我,捧起我的脸,眼尾泛红,目光是病态的偏执,声音里带着撩人的蛊惑:
「妙妙姑娘是怎么猜到我心思的?
「我把妙妙画满这间屋子,妙妙就是我的了……可好?
「明日就开始画,行不行?
「妙妙、妙妙……」
10
年少的疯子,也还是疯子。
秦宴说着狂悖不堪的情话,唇齿间不断呢喃着我的名字。
声音渐哑,语气渐轻。
我扬起脸,看到少年漆黑的眸里正翻涌着深渊般的欲念。
「秦宴,你从前真是好会装。」
我将唇贴在他的侧脸上,轻吻浅啄,又迅速离开。
秦宴错愕了一瞬。
很快,他眼尾的红晕便越来越浓。
再开口时,他嗓子已经哑得不像话:
「妙妙姑娘是小狸奴投生的吧?
「将人心勾缠走了,却又不负责了?」
他问得无奈又委屈,卑微又放肆,迷乱又克制。
我但笑不语,只戏谑地望着他。
我一直不知道秦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盯上的我。
他此刻,是已经把我当成他的私有物了么?
那样说来,他盯上我,便该是在更早以前……
11
我仔细回想。
在我及笄之前的年岁里,与秦宴的交集大约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一个冬日。
那年,下了一场瑞雪。
我带着侍女出门赏雪,本想寻个僻静之地,却误打误撞,看到了秦宴。
他正被几个世族公子按在雪地里打骂。
我又惊又怒地扬声喝止。
那几人认出我的身份,碍于太傅府的面子,终于肯收手散去。
秦宴目光阴冷,始终绷着神色,固执地不肯示弱。
直到那些人走远之后,他才终于绷不住,咳了几口血。
血色殷红,落在皑皑白雪上,触目惊心。
我下意识扶了他一下,掏出帕子给他用,又吩咐侍女阿春去寻人帮忙。
可秦宴只踉跄了一瞬,便强撑着站回风雪里:
「不必。」
他垂眸盯向我手里那方沾染了他的血迹的丝帕,薄唇间溢出一丝自嘲的凉笑:
「苏小姐还是离我这种人远些,免得脏了自己。」
他说完便走,颀长单薄的背影与雪色融为一体。
那是我第一次记住他的样子。
倔强,阴郁,狠绝,孤独。
像是蛰伏的兽。
12
我与许多世家公子贵女们一同长大。
世家交往大多以利为先。
人们看不起秦宴,自然更不会去亲近他——这个贱妓所出,毫无希望的秦家庶子。
我却头衔颇多:
太傅府嫡长女、京城第一才女、未来的太子妃。
所以……
我一向是被众星拱月的那个。
而秦宴,一向是被孤立的那个。
京中世族就这么几家,年年盛事欢宴,总有碰面的时候。
自那次之后,我又远远地见过秦宴几次。
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淡淡看着远处的喧嚣,眼底偶然间会闪过一丝不屑。
我与他也有过眼神对上的刹那。
我会对他莞尔示意。
他则冷冷淡淡地错开目光。
有人在背地里讽他——
说他那张脸长得勾魂摄魄,像极了他那个花魁娘亲,一瞧就是下贱胚子。
我听着不爽。
这种时候,我那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便能派上用场。
我会端着最文静贤淑的样子,笑不露齿,礼貌地提醒那些人:
「闲谈论人非,实非君子淑女所为,慎言慎言。
「与其背后说人短,不如静坐思己过。」
……
有时,我厌烦得很了,也会勾着笑,懒洋洋地给那些人讲:
「听说啊,地府分十八层。
「第一层,便是拔舌地狱。
「凡是挑拨离间、多嘴多舌、诽谤加害、说谎骗人者,死后都会被打入这一层。小鬼会掰开那人的嘴,铁钳夹舌,生生拔下……但是又非一下拔下,而是拉长,慢拽……」
讲完,我面不改色,佯作淡然地摇扇饮茶。
天知道,我有多么厌恶他们的聒噪。
天知道,我每天装温良淑女有多累。
天知道,我烦得想拔了他们的舌头。
这招总是比温言温语的提醒更奏效。
每每我这样说,周围便会立时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只不过……
再奏效的手段,也偶尔会有意外。
那一次,旁人听了我的拔舌地狱之谈,皆收敛闭嘴。
可偏偏——
我背后却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呵笑。
我小心翼翼地回头……
居然瞧见了秦宴。
他不知何时来的,正站在我身后,一双深眸凝着我,似笑非笑。
世上最尴尬之事莫过于此。
我那时生怕他误会,急忙解释:
「秦少公子,我并非在背后议论你,我只是……」
可秦宴根本不待我说完,便薄唇开合,唤我名字:
「苏妙姑娘。」
我有些茫然:
「嗯?」
他问:
「若拔舌地狱是第一层,那后面的十七层呢,又是怎样的地狱?」
我答:
「第二层是剪刀地狱、第三层铁树地狱、第四层孽镜地狱……」
说着说着,我便意识到不对,赶紧停了下来。
我顶着京城才女的名头,读的应该都是贤者文章,诸子百家。
地狱之说,是我从杂谈野志上瞧来的。
偶然一句无妨,可要是再往下数,内容实在过于阴间,便与我的身份很不相宜了。
我有些气,偷偷瞪他。
亏我之前还暗中维护他,他竟想坑我?
秦宴却勾了勾唇角:
「若有朝一日,能听苏妙姑娘将后面十八层的故事都讲完就好了。」
……
这便是我及笄之前,与秦宴的两次交集。
第一次,我撞见他雪中的狼狈。
第二次,他看透我人前的伪装。
所以,这个狼崽子,居然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了?
13
从记忆中回过神来,窗外日头已经西斜。
我从秦宴的怀中离开,手中捏着他给我的那本《川域志》,随手翻了翻,倚门而笑:
「秦宴,想知道第五层地狱是什么吗?」
他垂眸盯着我,一开口,尾音上撩:
「怎么,妙妙姑娘终于愿意讲了?」
我却道:
「下个月的秋猎围场,你我联手,若能赢了容玉太子,我便讲给你听。」
……
这年的秋猎,会有一场刺杀。
容玉太子在这一局里救驾有功,经此一事,此后更是深得圣宠。
可其实,容玉早就获悉了敌国那些刺客们的计划。
他故意隐瞒不报,就是为了博得救驾之功。
而我那庶妹苏明颜,更是心思歹绝,她避险途中,居然趁乱把我推到了刺客的刀下,意图要了我的命。
是秦宴替我挨了一刀,又反手把那刺客杀了。
可那刀上有毒……
我至今记得他衣袍染血的模样。
上辈子,拜这一刀所赐,秦宴落下了病根。
以至于后来,他即便位极人臣,寻尽天下珍药,也终究寿数难续。
这一世——
我要让苏明颜和容玉太子一起,来偿还这一刀的债!
只不过……
我却忘了,秦宴这疯子,向来是个贪心的。
他凑近我,扬唇一笑:
「妙妙,不够的。
「我若赢了他,你得在洞房之夜的喜床上讲给我听,才行……」
14
秦宴厮磨的气音在我耳边掀起热浪。
我笑着答应他:
「好,听你的。」
抱着书册扶梯而下时,我听到秦宴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忽然有些相信妙妙姑娘先前的那些梦话了。
「妙妙姑娘忽然转了性,待我这般好,是因为在那场梦魇里,有所遗憾吗?」
我回眸望他,诸多心酸,化作一句:
「是啊,梦里遗憾颇多。」
只见秦宴懒洋洋斜靠着门,笑弧惑人:
「看来,那确实不是什么好梦。
「不过,我曾梦过妙妙上千遍,妙妙这才只梦了我一遍。
「依我看,妙妙不如摒弃忧思,乖乖吃饭,好好睡觉,再多梦我几次。
「说不定下一次,便是好梦了。」
我鼻子一酸,不禁点头称是。
我知他一直望着我,可我却不敢再去看他灼热的眼神,匆忙应过,便赶紧走了。
我生怕再待下去,会在他面前哭红了眼。
15
上一世,他也说过不少情话。
只是我从来都不大相信,自然也鲜少回应他。
我见过他杀人时血溅满身的样子。
也见过他面无表情地将人四肢斩下,泡到酒缸中施以极刑的残忍手段。
所以,他的情话,在那时的我听来,更像疯话。
尤其是当我得知他爬上高位的手段之后——
秦宴少时受尽欺辱凌虐,伤病诸多。
为了韬光养晦,他故意隐忍不发。
但他其实从小就偷偷地习文、练剑、拉拢人才。
他在暗中,伪装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专门与京城权贵们做生意敛财。
看似卑贱如泥的少年。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堆金砌玉。
一切,只差一个青云直上的机会。
机会随时可以谋。
可他的余生,却被我毁了。
秋日围猎的那场刺杀,他救我或许只是顺手。
谁知那刀不惹眼,那毒却致命,短短几年,便送他去见了阎王。
他委实是赔大发了。
起初几年,他尚可以靠药物维持,装作身无大碍的样子,在朝中肆意翻弄权柄。
没人看出他的破绽。
而我,是在太傅府落败,被罚没入贱籍的那一年,才被秦宴带走的。
当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那其实已经是秦宴生命的最后一年。
我被他囚在深苑里,听到了从他房中传来压抑不住的咳嗽,闻到了他院子里经久不散的药气,又看到他呕血之后来不及换下的脏衣,才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倒也无意瞒我,甚至还学会了挟病图报:
「我都快死了,妙妙还不肯说两句好听的哄哄我?
「真是无情,你就那么喜欢太子?哼,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人说,冲喜能续命,要不……妙妙给我冲喜试试?
「不答应就算了,别用那刀子似的眼神瞪我。
「我这府邸是能吃人吗?你就那么急着离开?
「等我死了,再放你走行不行?」
其实我与太子,顶多算是青梅竹马之谊,谈不上喜欢或爱。
更何况,当我得知是太子害死我弟弟的那一刻起,对他就只剩下恨了。
秦宴却闲来无事总会酸上太子几句,一边酸还一边观察我的神色。
我不信秦宴是真的看上了我,我猜他大概是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多年的筹谋,全毁在了救我的那一刻。
所以他才囚我于深苑,要我陪着他,伺候他,以满足他那偏执的私欲。
最无语凝噎的是……
我从小养在深闺,在太傅府落败之前,连一丁点的重物都没提过。
他却非要教我练剑。
那剑沉得要死,我拿一会儿就手酸,赌气扔在地上不肯练。
秦宴难得在我面前阴了脸:
「匕首你嫌短,刀剑你嫌沉。
「暗器你嫌丢不准,射箭你又嫌胳膊疼。
「妙妙的手真是矜贵,到底教什么,你才肯学?」
我反唇相讥:
「我学那些做什么?像你一样,动不动就杀人吗?」
他笑了,大约是气笑的。
因为他笑过两声之后,脸色便骤然苍白,蹙眉重咳,竟呕出一口血来。
我以为他终会放弃的。
可他缓过来之后,却又淡然地拭净唇边血线,让我继续,还笑吟吟地威胁我:
「妙妙今日若是还学不会摘叶飞花,便伺候我沐浴吧,可好?」
我心里骂他是疯子。
可他这话却总有奇效。
为了不去伺候他沐浴更衣,承欢身下,我到底学会了不少东西。
只是渐渐地,我眼看着秦宴从一个风华绝艳的公子,变成了垂死挣扎的困兽。
他的手越发无力。
他握不稳剑了,也拿不动弓了。
终于轮到我笑话他:
「你为奸作恶,即使身居高位,活着又有何趣?待你死后,世上没人为你哭,他们只会欢呼。」
秦宴盯着我,反问:
「你也不会哭?」
我连想都不想:
「不会。」
他失神了一下,才缓缓嗤笑:
「嗯,那活着确实无趣。」
我便又道:
「那你为何还活?
「不如断了药石,死了干脆。」
他被我咒了也不怒,只是阴郁的脸上满是无奈:
「没良心的小狸奴,我若死了谁来护你?
「教了你半天,你却连只鸡都不肯杀。
「我若不把那些想害你的人都杀尽,又怎么敢死?」
一般时候,他喜欢叫我妙妙。
他说这名字像在唤猫。
所以,当他偶尔不怎么高兴时,便喊我小狸奴。
等到秦宴终于肯放我离开的那日,他已是病容枯槁。
他连说话都费极了力气,眼神却偏偏还带着狠意:
「我死后,你便不许再怨我、厌我了。
「否则我便化身厉鬼,夜夜逢你春梦,与你欢愉纠缠,扰你不得安……」
说到一半,他又忽然顿住。
终究苦笑一声,无奈地红了眼:
「罢了。
「你放心吧,这个世上不会有鬼。
「也不会再有我了。」相关Tags:生命喜欢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1864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