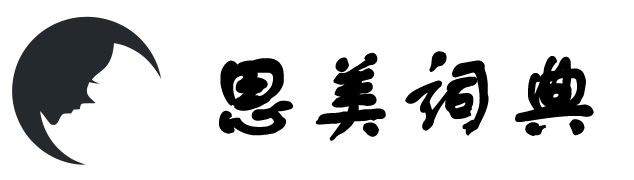余甜拢了拢身上的棉服,也不由自主的加快脚步。
忽然,她的视线被一个方向吸引了。
岔路口的那颗大柳树下面围了不少的人。
大树上面还挂了一个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几个大字,“算命看相”。
遇见同行了?
这些年以来,玄学衰微,真正的玄门中人越来越少,余甜跟着师父十几年,见过的同行屈指可数。
她来了兴趣,也凑了过去,想瞧一瞧究竟。
被围在中间的是个中年男人,他的手中握着不少卡牌,给其中一个老太太看了几张卡牌之后,便顺利的说出老太太的姓氏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
余甜听的直皱眉,通过相面能看出兄弟几人,儿女几个,这都不奇怪,但能看出人的姓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个中年男人哪是算出来的,卡牌上的字都是有规律有章法的,他通过卡牌的辅助,然后通过话术引导,再通过老太太的回答经过信息整合得出来的结论罢了。
这些,老太太是根本不知道的。
她以为中年男人真的是算出来的,奉为神明,连着叫了好几句大师。
中年男人见老太太上勾了,继续忽悠“老人家,你前面的苦受完了,往后都是享福的命了,不过......”
他说着话锋忽然转,惋惜的叹了一口气。
“你今年会有一个坎,如果过的去,就能长寿无忧,但如果过不去......”
老太太脸色刷白愣在原地,“还......还有救吗?”
“你既然碰见我了,就是缘分,这事我还真的有一解法。”
“求大师救命!”
中年男人从包里面翻翻找找,拿出来一个符纸,“这个符纸你拿回去,压在枕头下七天,然后在第七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化掉,符灰化水喝掉,可保你无忧。”
几句话的功夫,老太太便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她没立即晕倒都是心理素质过硬。
“谢谢大师。”
她颤颤巍巍的去接符纸,却没有想到中年男人手一拢,直接把符纸又收了回去。
“符纸一千。”
一千能换后半生无忧,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划算。
“好!我要!”
老太太没细想,就从衣服里面掏出一个手帕,手帕里面包的厚厚一叠全是钱,有零有整。治病还得靠医生,至于符纸什么的,着实没什么大用处。
更何况,这个中年男人的符纸就是随便乱画画,压根没有什么效力。
老太太刚想张口细问,人群中有一个人先出了声,“咦,这不是镇东头老纪家外孙女吗?我说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中年男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呢,一个毛丫头片子懂什么相术?”
人群中更是嘘声一片。
“小姑娘家家的,怎么不学好......”
正在这个时候,老太太的手机铃声大响,将乱糟糟的声音一下子压下去了。
来电显示是儿子的名字,老太太立马接了。
“妈,上回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医生说你肝脏上出了一点小毛病,幸亏发现的早,等我明天回去接你。”
“......”老人愣住了,她这才想起来前些日子被儿子接进城里的时候,儿子带着去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她当时还不以为意,觉得儿子是在浪费钱......
独属于老年机的大音量清清楚楚的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
谁也没想到,余甜说的竟然是真的,一时间人群中静默无声。
中年男人则是偷偷的准备开溜,被余甜抓了个先行,“叔叔,你先别走,我也送你一卦。”中年男人打的就是算命相面的旗号,他肯定不会让这个砸了他生意的小丫头帮他算的。
他挥了挥手,“不用不用,我还有事。”
看热闹的人则是纷纷起哄,“就听听呗!这小姑娘说的挺准的。”

余甜才不管中年男人愿不愿意听呢,缓然出声,“你帝座泛黄,今天恐怕有牢狱之灾。”
中年男人听不懂余甜说什么帝座不帝座的,但后一句是听懂了的,气急败坏地嚷嚷,“你......你......你这小姑娘,坏我生意还不够,还要咒我?大家评评理!”
这次大家都噤了声,没一个人跳出来帮中年男人说话。
谁是神棍,谁是真正的大师,大家心里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中年男人嚷嚷了一会儿,见没人理他,便背起东西,灰溜溜地准备溜走,刚拨开人群,一辆警车呼啸而至。
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冲过来揪住中年男人的衣领,“警察同志,就是他骗了我老婆的钱!”
中年男人被钳制的死死的,压根挣脱不开,最后还是被戴上铐子塞进了警车。
围观的人散去之后,余甜才看见不远处还停着一辆车,车子旁边站着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女人。
不是别人,正是余甜的后妈姜若兰。
姜若兰到了有一会儿了,刚才的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视线相遇,姜若兰快步走了过去,叫了一句,“小甜,你跟阿姨回去吧,一直在这里住着这不是事。姥姥已经走了,她肯定也希望你过得好,你说是不是?”
“就算跟家里有天大的嫌隙,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爷爷住院大半个月了,情况一天比一天差,医生说可能这个冬天就过不去了。他人还没出院,你爸爸也进医院了......”
像是怕被余甜打断一样,姜若兰的语速很快,说到最后眼圈有点儿发红。
“好。”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1440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