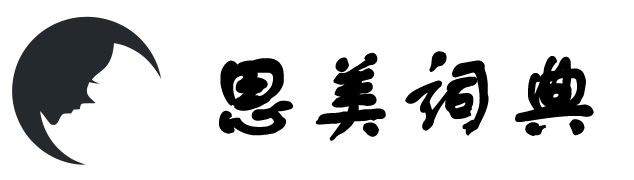怀信顺着她方向看了眼,只觉那个身影很是熟悉。
似乎……是天帝。
殿外。
徐长明负手等候,见阙月及近,笑意愈发温润:“去何处说?”
阙月言简意赅:“泽芳地。”
徐长明没再多言,捏了个传送决。
泽芳地内。
这是阙月掌管的地境,白昼永恒,各类珍惜草木茂盛生长。
她与徐长明一起,现身在一方凉亭当中。
徐长明环顾,不由得感慨:“自你千年前去渡情劫,我再没机会来此地。”
阙月不语,先在石桌旁落座,替自个儿沏了壶花茶。
“许久不见,帝君就只有这句话想说?”
徐长明转身,静静凝向阙月:“若你还在怨那千年的遭遇,只能说你这情劫没渡好。”
闻言,阙月不由得发笑。
她眼含轻讽:“帝君倒是渡清楚了,不也照旧同他们玩弄我于股掌之中么?”
这次轮到徐长明沉默。
二人四目相对,气氛略微凝滞。
忽地,徐长明面上一松,又变回了那副老好人的模样。
“本君也是想趁长泽忘记你时替你了断,否则你还不知得轮回几趟、蹉跎多少年才能放下,那泽芳地该当如何?”
阙月听着,面上却无甚波澜。
她端起茶杯轻抿了口,尔后才缓缓道“帝君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身而为神,她的职责便是孕育世间奇药,看管人间疾苦。
情劫渡一千年,着实不太像样。
可若是徐长泽从开始便对她无意,就不会有那七百年的恩爱。
后三百年,她也不会要靠玉竹算计,才能彻底放下。
所有磨难,都自有它的用处。
阙月垂下眼帘,拇指摩挲着茶杯:“所以天帝今日等我,就是想与我叙叙旧?”
“差不多。”徐长明道。
阙月抬眸,嘴角噙笑:“我想去天池一趟。”
徐长明眼眸微眯,带着股无形得威压:“阙月上神这是何意?”
阙月不慌不忙,起身迎上徐长明双眸。
“帝君不必这般紧张,我只是要去取回遗落在天池结界内的真身,并不做他想。”
“至于徐长泽——不管他是否想起我,我都不愿跟他有任何牵扯。”
听到这番话,徐长明才又慢慢温和。
他眯眼笑着:“如此便好,本君也可放心了。”
言罢,徐长明便转身告别。
阙月望着他背影,终了还是忍不住问:“帝君如此担心我与徐长泽纠缠,是为什么?”
徐长明头也没回,声音悠悠传来:“本君只要诸神各司其职,三界安定。”
言外之外,还是在介怀因阙月因情劫耽误了职责。
她不再言语,只是目送徐长明远去。
……
待回方寸山,已快天明。
虚空宫仍点着灯火,隔远远的,阙月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徐长泽站在殿门前,长身玉立。
阙月秀眉微蹙,上前轻唤了声:“长泽神君。”
徐长泽身形一滞,徐徐转身,看向这个时辰才回的阙月:“上神去何处游玩了?这样好的兴致,竟彻夜未归。”
这话说得有些太没界限,阙月眉头不由皱得更紧。
她不悦盯着徐长泽,话里夹枪带棒:“长泽神君何时管起本君私事来了?”
徐长泽默住,神情被说得有些不大自然。
而阙月懒得同他纠缠,索性敛了敛神,直奔主题:“长泽神君来此究竟有何事?”
徐长泽也不似之前那般逾矩,虽觉留在这里的理由荒唐,但也如实道来:“我心中有一惑——为何同活万年,我却从不知天界以南有座虚空宫,也从未听说过阙月上神?”
“旁人多少还听过上神名号,只有我,对上神一无所知。”
“阙月上神可告诉本君,这究竟是为何……”
阙月静静听着,不做打断。
她看着徐长泽越显困惑的眉眼,不由得在心底感慨,这忘情水还真叫徐长泽将她忘了个一干二净。
这样也好……只是不知为何,心底隐隐有些落寞。
阙月深吸气,压下那些不该有的情绪,打断了徐长泽的问话:“神君多虑了,本君从前深居简出。你没见过实属正常……”
“这不一样!”
话还未完,就被徐长泽急急打断。
他朝阙月逼近一步:“可阙月上神的眉眼,又像极我从前认识的一个人……”
说到这,徐长泽的话戛然而止。
他脑中猛地闪过时吟的面容。
很快,他便觉得自己荒唐。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天神,一个是卑贱低微的野草,两人长相也并不相似,可为什么他总是将这两人想到一起?
徐长泽困惑不已,太阳穴也似针扎般疼。
而阙月还在询问:“长泽神君是觉得我像谁?”
徐长泽头痛更加剧烈,他抬手用手掌抵住太阳穴,心底似有什么破土而出。
曾游历过的山河、相思树下的誓言、还有滚滚而来的天雷……忽如走马灯从她脑中掠过。
还有每一声长泽,与每一声……阿吟?
徐长泽瞳孔猛地收紧,一声低唤破喉而出:“阿吟?”
阙月神色微变。
而徐长泽看向她的眼神愈发恍惚,她正欲出手,一道身影似疾风般卷了过来。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zhufuyu/1762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