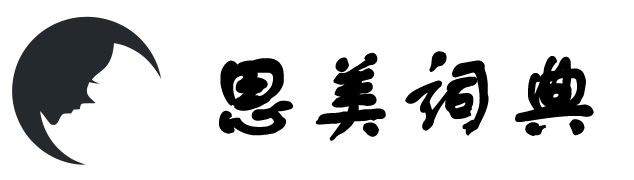康哥儿是谢家的子嗣,自然要上族谱的,只是族谱里明确嫡庶,想来这才是谢子安一直拖着没给康哥儿上族谱的原因。毕竟嫡庶不同,他看重康哥儿,不舍委屈这孩子。“你难道只听到我们说给康哥儿上族谱,没听到说抬丽娘为平妻?”谢子安阴着脸道。祝温卿淡淡一笑,“我同意了吗?”...
康哥儿是谢家的子嗣,自然要上族谱的,只是族谱里明确嫡庶,想来这才是谢子安一直拖着没给康哥儿上族谱的原因。
毕竟嫡庶不同,他看重康哥儿,不舍委屈这孩子。
“你难道只听到我们说给康哥儿上族谱,没听到说抬丽娘为平妻?”谢子安阴着脸道。
祝温卿淡淡一笑,“我同意了吗?”
谢子安怒斥:“何需你同意!”
“那你们且试试!”祝温卿执起面前丽娘喝剩的半杯茶,眸光一陈,用力扔到了饭桌上,砸到盘子里,立时碎成几片。
当的一声脆响。
好好的宴席,立时狼藉一片。
“祝温卿!”老夫人怒喝,“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我不同意。”祝温卿微笑道。
“这事,我已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呵,日子过得太安稳了,忘记之前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了?”祝温卿目光扫了一遍在场的人,嘴角冷冷扯了一下,“还是说,你们真当他死了?”
“他现在已经是穷弩之末,你休要依仗他。”谢子安话虽这么说,但气势已经短了一截。
谁想招惹那疯子,一个不高兴就屠你满门的恶棍。
大夫人咳嗽两声,而后开口道:“三弟妹,今日是为送成哥儿进考场做的家宴,其他的事,还是先不提了吧。”
老夫人沉了口气,“便先不提了。”
只是宴已毁,也没法再继续了。
祝温卿默了片刻,道:“康哥儿是三爷的长子,又是在他患难的时候生下来的,与他一同吃了不少苦,我也心疼这孩子,但嫡庶有别,老夫人不是最看重这点。不过族谱还是要上的,按着规矩需得等嫡子出生上族谱,而我腹中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这次便给康哥儿行个方便,一起上了族谱吧。”
“你还没生,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怎么上族谱,再说了,他又不是……你心里明白!”谢子安喊道。
老夫人也皱眉,“自来就没这规矩,但祝氏你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不就是为了给腹中孩子一个体面的身份。我们即便顺着你,但这般不守规矩,其他世家也不会同意。”
大荣开朝封八世家,八家同气连枝,共享宗庙,族谱也供奉在一起。
悠悠数十年,直至今日,八世家为了对抗后来者,仍旧抱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年靖安侯携十万大军出征塞北,十万将士全殁在那儿了,事后责任全归咎于靖安侯府,这么大的罪名,诛九族都够了,但在其他世家的力保下,靖安侯府竟没被削了爵位,只等小一辈成长起来再袭爵。
这便是八世家。
按着祖上的规矩,谁家添了男嗣,需得其他七家家主一起打开藏族谱的匣子,在七家见证下拜过祖先而后上族谱。
也正因为如此,祝温卿才看重这个身份,只要上了族谱,这孩子便是靖安侯府三房嫡子,堂堂正正,体体面面,没人敢再猜忌这孩子和司桁的关系了。一旦上了族谱,靖安侯府也不能私自改动,而且八世家为了后继有人,也会保护这些小辈儿。
谢林成,谢林羽便是,祖辈父辈犯下大错,他们一个继续在国子监,一个继续在武教坊,至少在学业上没有受影响。
这就是今天她拖着沉重的身子过来的目的。
“若他们同意呢?”祝温卿反问老夫人。
老夫人皱眉,“荒唐,怎么可能!”
“若他们同意,侯府没话说吧?”
老夫人冷嗤,“你要真有这本事,我还能说什么。”
祝温卿走后,谢子安绷不住了,“娘,万一她真有这本事,难道我们真要容下那孽种,列祖列宗也不能答应!”
老夫人好笑道:“即便她背后有东厂,有司桁,但八世家可是连皇上都撼不动的,你觉得有可能?”
谢子安一想也是,“那康哥儿的事?”
“只等那司桁一倒台便休了她,到时你扶正丽娘就是。”
谢子安回头握住丽娘的手,“听到娘的话了吧,我不会委屈你的。”
丽娘一脸感动,“若不是为了康哥儿,我也不想去争这位子,只要三爷心里有我,我便知足了。”
二爷谢子轩一直沉着脸,听到这里,实在听不下去了,腾地一下站起身。
“一个大男人想着法子的对付一个女人,这也算本事!”
说完,他大步离开。
回到西院,祝温卿从箱底翻出一块腰牌。
“子衿,你陪我进一趟宫。”祝温卿道。
子衿自是没话说,只点了点头,但谨烟急了,“姑娘,你发烧了不成,说什么胡话呢,那宫里是您想进就能进的?”
祝温卿笑,“我自然有办法。“
“可你现在这样……”
“我没事,你安心在家等就是。”
趁着夜色,祝温卿自后门坐上马车,朝着宫门去了。
她手里的这块腰牌,正是之前在紫云庵山崩的时候,她救了太后,太后给了她这一块腰牌,说是日后若有求于她,可拿着这腰牌进宫。
祝温卿去后,谨烟实在不能安心,思量半晌,还是戴上纱帽出门去了。
从太后的洛寒宫出来,夜已深,月正明。
皎皎夜空中,一轮明月,繁星无光,略显得孤寂。月光如霜,铺在青瓦红墙上,铺在这条狭长的甬道上,一阵风过,带着些许寒凉。.
子衿被挡在宫门外,只一小太监在前面为她掌灯。
太后问的那句话犹在耳边:你就这么恨他,要他的孩子随别人的姓,一辈子不认他?
她回道:我不恨他,但我的孩子能堂堂正正姓司吗?
高高在上,尊贵至极的太后,她沉默了,她也不能给她一个保证。
许久,太后叹了口气:“许,也是好事吧。”
祝温卿回过神儿来,见一人站在不远处,一身玄衣,带着凛凛威势,在这初入秋的季节里,满身寒意。
那小太监是个识眼色的,回头冲祝温卿行了礼,便回去了。
祝温卿沉了口气,朝着司桁走过去。
“谨烟找你了?”
司桁一脸阴沉,“你要不要告诉我,你进宫见太后,做了什么?”
祝温卿微微一笑,“何必明知故问,想要我亲口告诉你,那好……”
“闭嘴!”
祝温卿仍是笑着,这时风吹过,吹落墙头的枫叶,打着旋落到她面前。
祝温卿一手接住,枫叶已经红了。
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而她,没剩多少日子了。
“不过你不是被皇上禁足府中了么,还能自由出入宫里?”
况他被禁足,也是因为夜闯宫闱。
这么屡教不改的,皇上不杀他都对不起那弑杀的名声了。
司桁冷哼,“我的事不劳你操心。”
“这话说得好,我的事也不劳你操心。”祝温卿回怼道。"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2036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