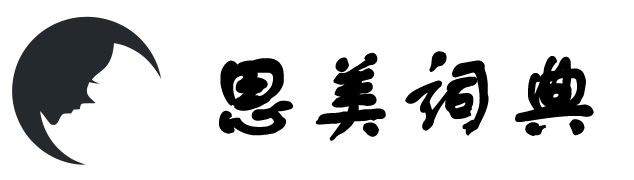我扫向林宗易的合约,是港口贸易的项目。现在林宗易正急需一个光明正大的幌子掩护自己进出货物,程氏就送上门了。
出事了是程威的麻烦,没出事是林宗易的油水,他一心要拿下程氏,估计就看中了这块。 签完合同,保镖叫来荷官开始玩牌,是清一色的男荷官,我这才醒悟程威所谓的不好女色,原来是好同类。 他笑眯眯望着一个长相最白净稚嫩的小鲜肉,那眼神我鸡皮疙瘩起了一片。 程威赢了十几把,他一开心,拧了一下发牌荷官的屁股,冯筠淮和林宗易视若无睹,连续给程威喂牌。 程泽去了一趟洗手间返回包厢,很快我就感觉到有一只脚在摩挲我的小腿,我躲开,脚穷追不舍,沿着我膝盖往上厮磨,反复徘徊。 蹬鼻子上脸了,我忍无可忍瞪着程泽,“谁的蹄子!” 他专注研究程威手头的牌,没反应。 林宗易甩出一张红桃A,他问我,“怎么。” 我深吸气,搬椅子挪到他身边更近的地方,“没怎么。” 消停没一会儿,那只脚又追上来,可程泽和我的距离是绝对碰不着了,除非他先摩擦林宗易,显然他不敢太胡来,我意识到不是他,视线定格在冯筠淮。 他从容淡定审视着手上的同花顺,他稳赢,可迟迟没出,像在走神。 我小心翼翼掀开落地的桌布,一只白皮鞋脱在一旁,里头没脚,果然是冯筠淮。 我扭身子,朝向林宗易,腿从桌下果断撤离。 程威中途离开包厢接一通电话,程泽接替他,林宗易忽然抽出中间的牌反扣在桌上,“斯乾,根据池里的底牌,我猜你缺红桃J或者黑桃K。” 冯筠淮似笑非笑,“宗易要喂我牌吗。” 林宗易意味深长叩击着那张牌的背面印花,“输我这么多局,你也该赢一回了。” “我输了吗。”冯筠淮眼底漾着精明的寒光。 林宗易说,“早晚而已。” 冯筠淮看着他掌下的牌,“你准备喂什么。” 林宗易撅开一点边角,是红桃,他说“红桃J。” 冯筠淮耐人寻味笑,“宗易果真了解我,被你了解,不是什么好事。” 冯筠淮毫不疑心林宗易的用意,他把牌搁在荷官面前,“要他的红桃J。” 荷官问他反悔吗,冯筠淮回复不悔,荷官扣住,让林宗易撂牌。 林宗易一翻,竟然是红桃K。 他勾唇,“斯乾,对不住了。” 这把是压轴局,一百万的码。 荷官也摊开冯筠淮交出的一副牌,荷官也愣了。 冯筠淮从池底拾起一张,加上林宗易扔掉的,拼在一串又是同花顺,他神情玩味,“我正好也缺红桃K。” 林宗易微眯眼,端详着牌面,他顿时笑了,“斯乾,欲盖弥彰玩得很漂亮。” 他话音才落,食指轻轻一转,亮明最后的底,也是一张红桃K,“我坐庄。” 坐庄预留一张牌,倘若正巧是对方所需的,算是炸弹,对方等于诈赢,当场输掉两倍。 52张牌,天方夜谭的难度,冯筠淮押对了,末了还是林宗易再次反将一军。 冯筠淮目光锁定在牌面,他笑了一声,“宗易你的声东击西更高明。” 程泽目睹这一幕,他发呆好半晌,我知道他惊住了,互相猜心的把戏,是商场最难的把戏。也亏了他们让着程威,不然程威十架飞机都赔光了。 程威打完电话回到包厢,我起身去洗手间方便,关掉水龙头的一刻,我无意发现地面有一束人影逼近,而且是男人的影子,我猛地一抖,本能抬起头,镜子里投映出一张面容,烧成灰我也能从火葬场里认出的面容。 我慌张转身,他手臂伸向我,我抡起胳膊搪开他手,“冯筠淮,这里是女厕,你发什么疯?” 我四下看,空无一人,只有我和他。 我往女厕门移动,“你卑鄙恶心。” 他饶有兴味观赏我发脾气,“林太太当初设局套我,都不觉得自己卑鄙,我又算什么恶心。” 我指着他被西裤半掩的白色袜口,“你洗袜子了吗,就拿它蹭。” 冯筠淮没想到我在恼他的袜子,而不是恼他刚才戏弄我,他一时皱着眉头,“什么。” 我说,“你袜子脏,恶心。” 他低头看,我在这工夫拔腿就跑,冯筠淮十分敏捷一把搂住我腰肢,贴向自己胸膛,他的脸与我的脸近在咫尺,“安卿,你耍我是吗。” 我冷漠偏头,“冯先生当梁上君子当上瘾了?” 他挟持着我一步步倒退,退进安装了马桶的格子间,嗅着我头发散出的茉莉香,“林太太的情史很厉害,今天也算新欢旧爱齐聚一堂。” 我冷嘲热讽,“那你还抱着,别污染了冯先生头上的草原。” 他舌尖掠过长发盖住的若隐若现的肌肤,“林宗易的草原,比我繁盛。” 我顷刻间翻脸,试图甩他巴掌,他眼疾手快一扣,扣在我腰后,我手掌僵硬着。 冯筠淮的每一个字在四壁是墙的卫生间荡出回音,回音清朗低沉,蛊惑十足,“林太太做梦喊过我名字吗。” 我骤然想起那夜醉酒,恍惚是我在车上喊了冯先生,激发了林宗易的征服欲,才会突破协议夫妻的防线。 可冯筠淮如何得知。 我变了脸,“林宗易的司机是你的人?” 他笑意深浓,“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我恼羞成怒,“你诈我?” 他嘴角噙着一丝笑,“林太太可以耍我,我不可以诈你吗。” 我握拳死命击打他,冯筠淮钳制住我手腕,“林太太真舍得下狠手。” 我咬牙切齿,“对你没什么舍不得。” 他嗯了声,“不错,我记得林太太一向狠心。” 我抵御着他的撩拨,“你想怎样。” “不想怎样。”他回答得利落,动作也干脆,我抵御,他反而将我越发紧密地扼住。 我使劲反抗,“冯筠淮,你嗜好偷偷摸摸做贼吗。” 他轻笑,“明目张胆找机会,林太太有了戒心,还会落进我手中吗。” “冯先生也知道强求没意思。” “不。”他否认,“我不知道。世上最没有意思的是手到擒来的东西。” 卫生间的门在这时被一位珠光宝气的中年贵妇推开,冯筠淮一闪,隐匿在格子间的门后,连带我也被迫贴上大理石的砖墙,他手温滚烫,瓷砖冰凉,我整个人哼吟。 中年贵妇人路过这间门外,在台阶下停住,“林太太?” 我也看过去,“魏太太,您也在?” “我先生在411玩牌,您感兴趣来凑把手吗。” 我婉拒,“我牌技差,不去凑热闹了。” “这我可有耳闻。”她从包里翻找湿巾,“林太太在江都会所一晚输了四百多万呢。还好林董有得是钱,否则林太太恐怕给自家男人输破产了。” 我讪笑,“您别取笑我了。” 魏太太察觉我声音不太对劲,她靠近我,“林太太,您脸——” “别过来!”我大吼。 她吓一跳,惊惶退后,我脚底死撑,“您别管我……我便秘。” 她恍然大悟,“我推荐您看淮海医院的中医,我先生也经常便秘,应酬酒局天天大鱼大肉,肠胃能好得了吗。” 我强颜欢笑,“我记下了,多谢魏太太。” 她在镜前补了妆,又向我道了别,才慢悠悠离开。我松懈下来,手臂支着墙,冯筠淮的唇埋在我颈后,欲吻不吻,又不移开,喉咙溢出闷笑声,“便秘?撒谎精。” 我趁他不注意,扯下右耳佩戴的耳环,在他怀中翻了个身,锋利的针尖狠狠扎进他肩膀,鲜血刹那涌出,浸染过他雪白的衬衫,我丝毫不手软,向更深处刺,半寸银针被他皮肉完全淹没,殷红的血迹与白皙胀起的青筋相缠,冯筠淮仍旧维持我们最初纠葛的姿势。 他并未因疼痛而放手,冷笑凝视着我,“林宗易将林太太的胆子养得这样肥了。” 我浑身是汗,急剧战栗着,这副局面说不怕是假的,我以往多么恨他强迫,也只在背后耍花招,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发狠让冯筠淮见血,放眼江城谁敢让他见血,连林宗易都诸多顾忌,从未动用势力搞过他,他却在我手里见了血。 我面色苍白死扛到底,“你以后再纠缠我——” “动刀吗?”冯筠淮打断我,他拇指在肩头的血污上一抹,涂在嘴唇,强行吻着,一厘厘逼我吮干他唇齿间的血腥味。 “记住这个味道。”他脸上是极端的阴沉,“我从林宗易身上讨。” “斯乾。” 突如其来的熟悉的女声,使冯筠淮戛然而止,我也猝不及防地一激灵,捏住耳环的手松开,染血的银针坠落在地。 紧随其后是女人的尖叫,“你受伤了?” 冯筠淮望向门口的殷怡,她像是已经在那许久。 第69章 派林太太来惩罚我 冯筠淮若无其事整理着西装厮磨出的褶皱,他朝殷怡走去,握住她手腕,“你怎么来这种地方。” 江都会所没有发牌小姐,英雄本色在这方面玩得更开,也更香艳,跟着丈夫一起开开眼倒行,独身女人来玩,撞上那些输红眼的暴发户,很容易惹是非。 殷怡盯着他,盯了好一会儿,“你对我保证过。” 冯筠淮一言不发看着她。 她甩开他手,“斯乾,能给你的爸爸都给你了,我也一样。” 冯筠淮原本无波无澜的面孔在她说完这句皲裂出一丝喜怒不明的笑纹,“你要挟我吗。” 殷怡否认,“不是要挟。我需要一段踏实安宁的婚姻,基于此赌上殷家的全部,我唯一所求是一个值得我信任和依赖的丈夫。”她耐人寻味凝望他,“不用提心吊胆他的心思拴在其他女人那里,每每面对他,都充斥着隔阂与算计。” 冯筠淮也凝望她,“你口中这段婚姻,早在三年前我娶你就决定给予。而耗费了三年光阴的人,从不是我。” 话题引向她和纪维钧的奸情,殷怡顿时丧失了质问的底气,她抿唇不语。 冯筠淮用方帕捂住肩膀伤口,漫不经心的语气,“你去墓地了。” 殷怡脸上闪过惊讶,很快恢复正常,她郑重其事解释,“他在江城没有亲人,我只是尽最后的义务送葬。” 冯筠淮淡然笑,“我并非怪罪你,而是借此告诉你,人与人之间一旦生出牵扯,不是那么轻易能斩断。” 殷怡明白了,但寸步不让,“可斯乾,你必须断掉。”她越过冯筠淮看了我一眼,“包括任何令我不痛快的人。我会为你生儿育女,从此忠贞,弥补我对你的亏欠,我也要求你回馈我同等。” 冯筠淮眯着眼,“是协议吗。” 殷怡说,“我不需要建立在条条框框中的婚姻,最好是我们情感的共识。” 我恍然发觉殷怡变得冷静了,充满占有欲,短短一两个月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不相信没有高人指点她。纪维钧的离世让一场多年的虚情假意浮出水面,殷怡觉醒了,与其沉沦在不得善果的感情里,不如抓紧实际的丈夫,尤其冯筠淮还如此具有魅力,殷怡开始捍卫自己的婚姻扶上正轨,她已经认定我是妨碍她的假想敌。 幸亏我早早嫁给林宗易,不然只殷怡这关,我就不好过了。 冯筠淮云淡风轻开口,“我和安卿还存在没解决的事。” 殷怡半信半疑,“舅舅在场你们不能解决吗?非要私下见面。” 冯筠淮侧过身,他眼神带点玩味,不紧不慢扫过我,“可安卿想要单独解决。” 我错愕不已,万万没料到他来这一手泼脏的戏码,我当即激动反驳他,“你埋伏在女厕偷袭我,也是我要你做的?” 殷怡面无表情审视着冯筠淮。 他专注检查伤口,飘忽不定的余光实则定格在我身上,“难道不是林太太喊救命,吸引我闯入救你吗。” 冯筠淮有备而来,早已计划好被撞破之后的退路。 我深吸气,女厕没摄像头,我和冯筠淮各执一词,可全然死无对证。 我冷笑,“但愿冯先生的虚伪能演一辈子。” 冯筠淮翻转帕子,将血迹略微少些的那一面重新捂在伤口,不曾回应我什么。 殷怡没再追问,她明显倾向冯筠淮是真话,他比我底细清白,之前从没出过轨,遇到我才难得失控,一个一贯克制自律的男人,一个身经百战的狐狸精,换做是我,我也信男人。 斗不赢我躲得起,我正准备回包厢,伫立在走廊尽头的林宗易忽然喊我名字,“卿卿。” 我闻声望过去,他逆光而立,看不真切面容,一副轮廓如松竹一般温雅英挺。 我挥手示意,“宗易,我马上回去。” 我刚迈开步,冯筠淮像是刻意,又像是不经意,他挡住我去路,随手掏出烟盒,撕掉包装的塑料膜,他直奔墙角下的垃圾桶,顺势和殷怡拉开距离,不着痕迹靠近我,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卿卿。” 我情不自禁一抖。 记忆卷土重来,一句冯先生的卿卿。相关Tags:相思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202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