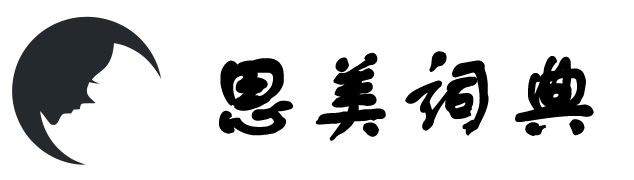话毕,再无多言,我挥手让琥珀继续帮我拆卸头上的钗环。大婚可真不是人能受的,顶了这一天的凤冠,脖子酸疼得很。
至于聂寒山身上也是一身酒气,略坐了几分钟后,自行去了后方浴室洗浴。
待到他一身水汽出来时,我已经屏退了左右,取了一本山闲游记的书斜靠在床头看着,浑然没有一点新娘子对夫君的娇羞。
聂寒山像似也累了,略看了我几眼,自顾自地上了床,扯过了锦被搭在了身上。
这张穿花百蝶千工床是我年少之时,母亲为我备嫁时,特意请了江南名匠苏大师历时一年半打造。
除了精美外,唯一的特点就是大,躺下两个我还绰绰有余。
聂寒山尽管身量宽大,但留给我的位置足够了。
见人已经睡下了,天色也不早了,我顺势放下了书,越过他下床吹灭了龙凤喜蜡烛。
「你干吗?」他不解地看着我。
根据京中习俗,新婚当夜的龙凤花烛需一夜点至天明,寓意夫妻恩爱、百年好合。
不过我与他之间倒也不必这些。
我缓慢地爬回床上,拉过了另一床锦被盖在了身上,淡淡地说道:「有光,我睡不着。」
我往里靠和他中间隔开了一大段距离。
虽是洞房花烛夜,但我们双方似乎也都达成了某种不可意会的默契。
聂寒山不会碰我这件事,在嫁进来之前我早已有了预料,此刻甚至还有些放松。
只是盯着床头的红绸,心头的惆怅难免消遣不过。
少女多心事,嫁人等于是第二次投胎,我也曾暗偷偷地幻想过自己未来的夫君会是什么样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坚毅果敢还是文质彬彬?他会是什么性子?我同他会是像姐姐、姐夫那样欢喜冤家、吵吵闹闹,又或是像爹爹和娘亲那样恩爱缱绻、举案齐眉……
如今一切都有了答案,我的夫君文才武略样样都好,可惜他心里早已经有了别人。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争风吃醋是天底下最傻的事情。
人心向来都是偏的,你做得再多,在他眼里或许还觉得麻烦。
就这样吧,不求疼爱,但求体面。
黑暗中,我闭着眼逼着自己入睡,泪水从眼角缓缓滑落。
没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连带着还有激烈争吵的声音。
我蹙眉,扬声对着门外喊道:「琥珀,出什么事了?!」
「芳院的赵妈妈硬闯过来,说是柳姨娘不舒服,非要找王爷过去!」琥珀的声音又气又急。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juzi/2017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