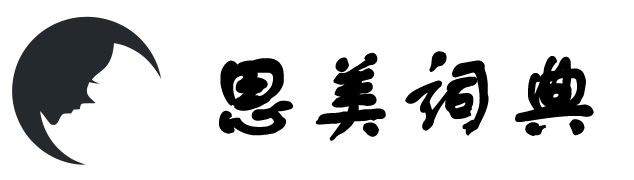扶着楹柱盯着已然平静下来的池面,不言不语,侍卫上前问要不要差人下去寻,我摇了摇头:「我自个来吧,他气得很。」
魏淮昀一身白衣斜倚在阑干边,捏着白玉酒瓶,尤为显眼。
魏淮昀听我恭维他,笑得像一只摇着尾巴的大猫,颇带宠溺地掐了掐我的面颊:「昔年公主一身银白铠甲,一匹雪白骏马,领万千将士夹道离开,我一刻也不敢忘,此后,不爱读书,只爱习武。」「今日不该在镇国公府说那样的话,叫殿下伤心,是我的不是。」
这皇子很有意思,居然是坐在花轿里来的。
闻言,我心里一刺,抬腿就要往军营方向跑,却又生生忍住,回身吩咐林琅:「安排人把粮草分发下去,清点人数,救治伤员,安抚百姓。让所有副将到军中来,我们集合议事,争取一个时辰内出兵,打个出其不意。」
行礼拜堂,推杯换盏,迎宾送客。
看着魏淮昀被扶远的身影,我心里有些说不清的烦躁,索性自己提着灯跑到厨房去,煮了一碗醒酒汤带过去。
洛水殿已然建好,到处燃着红烛贴着喜字。
彼时我才知道,魏淮昀当时为什么这么好说话。
「不提倒忘了,怎么那前未婚夫还说不得了,给我甩脸子?」魏淮昀眯着长眸质问着,「别是心里还记挂着,寻思再续前缘不曾?」
我笑了笑:「不可,我与大魏洛王已有婚约,怎可随意撕毁,与我们三方都无好处,况且我也不能过河拆桥。」
我眨巴了两下眼睛,意识到他说的是他自己,忍不住弯腰笑了起来,周遭的人都纳罕,我宫殿尽毁竟然还笑得这般开心。
「这样的条约签订,怎可不联姻巩固承诺,公主说,是不是?」我送给顾行止三个荷包。
第一个是我自己绣的鸳鸯戏水,鸳鸯绣成了小鸟,荷花绣成了枯叶。
这两个是我后来赶忙找宫中绣女所制,企图蒙混过关,给自己长点脸面。
他大约也觉着第一个丑,扔了去才没还来。
「我女红不佳,这不是我绣的,乃是我命宫中绣女所制。」承认自己偷奸耍滑到底有些害羞,我忍不住红了脸。
果不其然,魏淮昀嗤笑了一声:「不佳也算,便是绣出摊泥巴来都无妨。」
「绣,绣,绣。」我微微支起身子来,无奈哄他。
他满意地随手扔掉荷包,眯着长眸吩咐道:「该砸的砸,该烧的烧,一概不留。」
仆从们应声下去,我懒懒地再递上一眼瞧那些东西,一时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何感想。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便是如斯珍贵的血燕跟不要钱似的掺进药里,顾行止的祖母,还是病逝了。
听得这个消息,我手中的朱笔一时没抓紧,咕噜一声掉在了案几之上。
从前顾祖母待我是极好的,我从没想过这等将养着便会好的病症竟会要了她的命。
等到发引那天,我差人去搭了一棚路祭,特地换了身白衣打算去送殡。
魏淮昀一身红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来:「去哪?」
「镇国公家老太太病逝了,我去祭拜一下,送个殡。」
「镇国公?」
本怕他生事不愿多说,谁想他这等刨根问底,抿了抿唇,道:「顾行止的祖母。」
「我好巧也换了他血燕,老太太走了岂有不去送殡之理?」魏淮昀半靠着门框居高临下地睨了我一眼,神色似笑非笑。
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simeijiachuangyi.com/geyan/144394.html